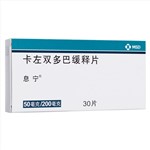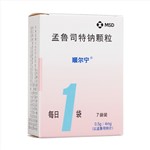2005年的夏天,李进带着家人回中国度假,这是他在国外呆了20年后首次回到祖国。令他惊讶的是,中国的面貌在20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是从2005年开始,由于李进部分负责管理阿斯利康的全球化学外包,为了跟踪合作项目的进展,每年需回到上海一到两次。他发现海归回国创业越来越成为趋势,“虽然当时做创新药的还不是很多,但CRO大都做得不错”,这一现象为李进回国创业埋下了伏笔。
1985年,从成都科技大学(现已并至四川大学)高分子科学专业毕业后,李进远赴英国,到英国阿斯顿大学大分子科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后至曼彻斯特大学的理论生物学博士后站继续深造。
毕业之后,李进加入其博士后导师创办的公司,在那里的十年多时间里,他带领研究了基于蛋白质结构的小分子药物设计项目。他的团队在一周内完成100万种化合物的筛选,且是业内首次使用计算机进行辅助筛选,这在当时引发了行业热议。从化合物库中筛选出种子化合物或者先导化合物进行优化,使之成为临床前化合物,这是新药研发的主要方式。此后李进加入阿斯利康,11年间,李进历任计算化学总监、化合物科学全球总监等多个研发要职。
李进真正萌生回国创业想法是在2009年,当时他作为阿斯利康全球高管参加成都高新区的国际生物医药峰会并发表演讲。通过这个机会,他感受到成都高新区的浓厚科研创新氛围,并且当地领导也鼓励李进归国创业。他同时看到,中国医药行业的大环境虽然以仿制药为主,但要做原创药的意识和市场都在觉醒当中。
中国把生物医药行业分成两种:一类是药物公司,有产品上市的;一类是服务供应商。其实在国外除了这两个之外,还有一类叫生物技术公司。此类公司兼具前两类的特征:既有自己的药物研发和产品线,又为其他公司提供技术服务。生物技术公司拥有自己独立的技术平台和研发团队,拥有知识产权,成都先导药物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先导”)就属于这一类。
1.扬帆起航
2012年3月,李进向阿斯利康递交辞呈,决定回国放手一搏。在成都高新区政府的帮助下,旨在创立世界级先导化合物筛选平台的成都先导正式成立,在大约1500平米的高标准生产车间内,扬帆起航。
成都先导立即以最快的速度招兵买马,7月装配好实验室,9月份完成了一支约60人规模团队的组建,并建立国内首家“DNA编码小分子化合物库合成与先导化合物筛选创新平台”。李进对成都先导的初步规划是这样的:“我当时的战略很简单,这个技术我们是国内首家,一定要尽快做起来,否则很容易就被复制掉。抓住机会,加快速度,最后把技术门槛做到一定程度,让平台到达进入国际市场的高度。”
建立DNA编码小分子化合物库合成与先导化合物筛选创新平台成为成都先导发展的重要利器。据悉,可提供该种技术服务的公司在全球范围里仅有4家有规模性的企业,其中有的企业还仅作为内部技术,并不提供对外服务,因此,成都先导成为全球能提供该技术的唯三厂家之一,是中国医药行业内的第一家。
众所周知,做创新药需要投入的资本很高,临床前和临床试验阶段尤其烧钱。成都先导的优势在于,其DNA编码化合物库中,每一个化合物都由一段已知序列的DNA片段进行分子水平标记,这使化合物分子筛选由传统方法的几个月时间缩短至两周甚至更短。
2013年底,成都先导利用创新平台合成了3亿个DNA编码化合物,2015年量级达40亿~50亿个,截至目前已达到800多亿个,预计2017年底这个数量可达1200亿个。平台分子数量级越高,对特定靶标或作用环节具有初步活性的化合物(苗头化合物)的发现率就可能越大,特别是对一些传统上极具挑战性的靶点。
李进透露,如果DNA编码小分子化合物库的分子数能达到一万亿个,苗头化合物的发现成功率能高达70%~80%。李进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短期目标:2019年底前将分子数做到一万亿个的水平。
2.扎实耕耘
回顾成都先导五年多的发展历程,创业初始对李进而言仍是难忘的艰难时期,处于婴儿期的成都先导面临着技术、资金、市场等诸多方面的挑战。“创业初期技术工艺不太流畅,用于建库的基本要素也不是很齐全,平台建立速度较慢。另外,我们的市场刚起步还没有打开,没有收入来源,依靠融资、政府支持的资金维持,基数本不大的团队粘性也不高,人员流动率很高。”
现在,熬过了低谷期的成都先导生命力显得更加强大。其团队已由原先的60人扩至210人,主要的研发人员中20%是博士,这其中近一半是海归科研者。李进在阿斯利康工作期间积累的不仅是丰富的研发经验,还有重要的人脉资源。成都先导首席科学家BarryA.Morgan是将DNA编码化合物库技术工业化的主要发明人,此前担任GSK分子发现部门副总裁,之前就与李进熟识,2015年退休后在李进的热情邀请下加入成都先导。成都先导化学总监及战略合作负责人AlexShaginian,此前担任过GSK分子发现首席科学家。
除了核心的DNA编码化合物库合成及筛选技术,先导在新药研发、创新商业模式上也做出了探索。为其他企业提供化合物筛选的技术服务给成都先导带来现金流。同时,成都先导还可以将自己的临床前化合物转让出去,其中既包括完全的转让加里程碑金以及上市后销售分成,也包括区域市场权利的转让。但是成都先导最终的目的是做出属于自己的新药,然后通过MAH制度实现上市销售。李进说:“成都先导最后要实现从一个生物技术公司向生物药物公司的转换。”
成都先导的新药研发瞄准肿瘤、心血管、炎症、呼吸道、代谢类及眼科疾病等重大疾病类型,内部在研新药项目逾20项。肿瘤药HG-1143、炎症治疗药HG-1078正处于产生临床前候选化合物阶段,还有1个新药处于先导化合物优化阶段。李进现在想的最多的一点,就是如何将这些产品快速推进临床试验。“对于新药管线,我们目前采用的策略是先主要集中在肿瘤,其他领域的产品研发出之后在进入临床前将其转让。”李进预计,成都先导最快在2017年年底提交自己第一个新药临床申请,“理想状态是一年报一个”。
近两年,商业合作模式创新对成都先导业绩的提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李进观察到,全球其余两家同类型公司的缺陷在于合作模式不够开放,最终的数据结果不会反馈至合作医药公司,参与度也不足。借鉴这一模式缺陷,成都先导在2015年提出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开发出包括DNA编码化合物库的设计及方案实施、利用DNA编码化合物库进行苗头化合物筛选及验证、先导化合物优化等新药研发合作或转让、特色化学或生物研发合作的四个合作模式。
当前,成都先导已建立了30多个伙伴关系,其中既有辉瑞、默沙东等跨国巨头,也有天士力、扬子江等本土企业和清华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这一创新为成都先导带来了明显的经济效益。李进表示,成都先导通过与合作伙伴的技术合作,能够产生足够的收入,并且他列出了这些数据:“通过技术平台合作,2017年上半年成都先导签了11亿元的合同,实际收入约5000万元。”
可以这样总结成都先导的商业模式:通过技术合作,保证有稳定持续的收入,而这个过程还可以提升平台技术和人才能力,从而让成都先导在新药开发的巨大风险前尽量做好准备,并不是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李进说:“这样比纯粹做药的风险低得多,即使新药项目失败了,还有技术合作的利润。一部分拿来支持运营,不总是靠融资。”
现在,李进有三个目标:在2019年底之前,成都先导的化合物库扩增到一万亿个;在新药研发上,争取每年都有一个临床前化合物进入临床;到2017年年底,成都先导签下的技术合作合同能达到15亿~20亿元。
本品适用于治疗原发性高血压。
健客价: ¥42适用于治疗男性秃发(雄激素性秃发),能促进头发生长并防止继续脱发。不适用于妇女和儿童。(详见说明书)
健客价: ¥158本品适用于治疗原发性高血压。
健客价: ¥49治疗绝经后妇女骨质疏松症以增加骨重,并降低骨折发生率,包括髋部和椎骨骨折(椎骨压缩性骨折);治疗男性骨质疏松以增加骨量。
健客价: ¥58适用于治疗男性秃发(雄激素性秃发),能促进头发生长并防止继续脱发。
健客价: ¥488本品适用于15岁及15岁以上成人哮喘的预防和长期治疗,包括预防白天和夜间的哮喘症状,治疗对阿司匹林敏感的哮喘患者以及预防运动诱发的支气管收缩。 本品适用于减轻过敏性鼻炎引起的症状(15岁及15岁以上成人的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和常年性过敏性鼻炎)。
健客价: ¥391.本品适用于2岁至14岁儿童哮喘的预防和长期治疗,包括预防白天和夜间的哮喘症状,治疗对阿斯匹林敏感的哮喘患者以及预防运动诱发的支气管收缩。 2.本品适用于减轻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引起的症状(2岁至14岁儿童以减轻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和常年性过敏性鼻炎)。
健客价: ¥30本品适用于儿童哮喘的预防和长期治疗,包括预防白天和夜间的哮喘症状,治疗对阿司匹林敏感的哮喘患者以及预防运动引起的支气管收缩。本品适用于减轻过敏性鼻炎引起的症状。
健客价: ¥411.原发性帕金森氏病; 2.脑炎后帕金森氏综合征; 3.症状性帕金森氏综合征(一氧化碳或锰中毒); 4.服用含吡多辛(维生素B6)的维生素制剂的帕金森氏病或帕金森综合征的病人 。(其它详见内包装说明书)。
健客价: ¥70适用于2型糖尿病患者;用于运动,饮食、药物控制不佳时,使用本药能起到一定疗效。
健客价: ¥58本品用于治疗高血压,适用于联合用药治疗的患者。
健客价: ¥431、本品适用于治疗和控制良性前列腺增生(BPH)以及预防泌尿系统事件:降低发生急性尿潴留的危险性;降低需进行经尿道切除前列腺(TLRP)和前列腺切除术的危险性。 2、本品可使肥大的前列腺缩小改善尿流及改善前列腺增生有关的症状,前列腺肥大患者适用于本品治疗。
健客价: ¥55用于1岁以上儿童哮喘的预防和长期治疗,包括预防白天和夜间的哮喘症状,治疗对阿斯匹林敏感的哮喘患者以及预防运动诱发的支气管收缩。 顺尔宁适用于2岁至5岁儿童以减轻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引起的症状。
健客价: ¥58适用于治疗男性秃发(雄激素性秃发),能促进头发生长并防止继续脱发。
健客价: ¥471适用于治疗男性秃发(雄激素性秃发),能促进头发生长并防止继续脱发。
健客价: ¥939原发性高胆固醇血症 本品作为饮食控制以外的辅助治疗,可单独或与HMG-CoA还原酶抑制(他汀类)联合应用于治疗原发性(杂合子家族性或非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可降低总胆固醇(T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载脂蛋白B(Apo B)。 纯合子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HoFH) 本品与他汀类联合应用,可作为其他降脂治疗的辅助疗法(如LDL-C血浆分离置换法),或在其他降脂治疗无效时用于降
健客价: ¥116适用于治疗男性秃发(雄激素性秃发),能促进头发生长并防止继续脱发。不适用于妇女和儿童。(详见说明书)
健客价: ¥1872非那雄胺片:适用于治疗男性秃发(雄激素性秃发),能促进头发生长并防止继续脱发。不适用于妇女和儿童。(详见说明书) 米诺地尔搽剂:本品用于治疗男性型秃发和斑秃。
健客价: ¥4186非那雄胺片:适用于治疗男性秃发(雄激素性秃发),能促进头发生长并防止继续脱发。不适用于妇女和儿童。(详见说明书) 米诺地尔酊:蔓迪用于治疗男性型脱发和斑秃。
健客价: ¥8371.原发性帕金森氏病; 2.脑炎后帕金森氏综合征; 3.症状性帕金森氏综合征(一氧化碳或锰中毒); 4.服用含吡多辛(维生素B6)的维生素制剂的帕金森氏病或帕金森综合征的病人 。(其它详见内包装说明书)。
健客价: ¥275非那雄胺片:适用于治疗男性秃发(雄激素性秃发),能促进头发生长并防止继续脱发。不适用于妇女和儿童。(详见说明书) 米诺地尔搽剂:本品用于治疗男性脱发和斑秃。
健客价: ¥1620非那雄胺片:适用于治疗男性秃发(雄激素性秃发),能促进头发生长并防止继续脱发。不适用于妇女和儿童。(详见说明书) 固肾生发丸:固肾养血,益气祛风。用于斑秃、全秃、普秃及肝肾虚引起的脱发。 米诺地尔搽剂:本品用于治疗男性型秃发和斑秃。
健客价: ¥11101.高脂血症。1)对于原发必高胆固醇血症包括杂合子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高脂血症或混合性高酯血症的患者,当饮食控制及其它非药物治疗不理想时,结合饮食控制,本品可用于降低升高的总胆固醇、低密度脂滑白胆固醇、载脂蛋白B和甘油三酯,且可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从而降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及总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比率。2)对于纯合予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患者,结合饮食控制及非饮食疗法,本品可
健客价: ¥28非那雄胺片:1.本品适用于治疗和控制良性前列腺增生(BPH)以及预防泌尿系统事件降低发生急性尿潴留的危险性。2.本品可使肥大的前列腺缩小。 盐酸坦索罗辛缓释胶囊:前列腺增生症引起的排尿障碍。
健客价: ¥6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