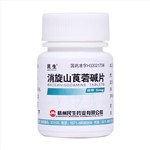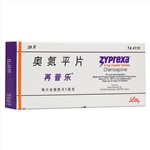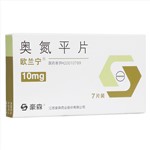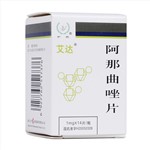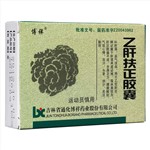寻访中国顶尖医疗团队——
本期人物: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脑血管专业组——曹勇
狄更斯《双城记》的开篇,“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似乎,这句话放在哪个时代都有意义。在当下这个举世浮躁的社会里,沉静下来做点事,不容易。风气裹挟下,急功近利的情绪无孔不入。曹勇摆摆手示意,不愿意再继续这个话题,“大家都知道的,没必要多言。”
“成功或失败,三分人事,七分天命。”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五病区副主任曹勇援引《曾国藩家书》里的话来总结。专业之外,他喜欢读历史、小说。当学生时最爱的小说——苏叔阳的《故土》影响了他做医生的选择。“现在看来《故土》写得有少许幼稚,但充满真情,如今回味起来仍让人感动。”
25年前,他过滤掉炼钢炼铁、计算机、金融,选择了医学。就像一场长跑,历风雨而不间断,人到中年,他愈发明白,更加珍贵的是长久的坚持,从医也是如此。
外人眼里,开早会、查房、出门诊、上手术、写论文……按部就班,周而复始,医生的工作和生活甚至极其单调。但在曹勇看来,这单调里也有着繁复的层次和深沉的质地。
忙碌还是像风一样扑面而来。
他裹了件大衣,往外走,185cm的身高,标准身材,步履轻盈,手里攥着一沓论文。在早会后手术前的半小时里,他要去研究所找谷博士商讨一下关于样本量估计、统计学差异等相关临床研究的问题。临床的事情太多,科研成了挤时间要做的事情。
病区里很少见他嘘寒问暖,他平素说,作为一位大夫,是要靠专业说话的,只会嘘寒问暖与邻里劝慰何异。
曹勇的门诊量不算太多,来就诊的患者多是脑血管病和老年神经肿瘤。
有位四岁多的小患者,片子上显示是血管畸形,但不能确定是哪一种畸形。曹勇说明情况并建议他们先去做造影,明确诊断,以便做下一步的治疗。尔后解释,如果是海绵状血管瘤可不必着急手术;如果是动静脉畸形,则要做手术或伽马刀治疗。脑动静脉畸形是脑出血主要的原因之一,出血可导致残疾,危及生命,需积极处理。
家长因为孩子小,很担心手术的影响,急忙问:“一定要做手术吗?要开颅吗?”“怎么做是大夫的事。你们首要的是先去做个造影,我们才能谈下一步的事。”
他的门诊里,常见这些片段,温柔而凌厉,贯穿始终。他并不客套,语气克制,声音低而有分量。通常,专业之外没有太多的话。
推门进来的两位女士,递了片子给曹勇看,“病人是我们母亲,急性脑出血,昨天晚上送到急诊室的,现在仍然昏迷不醒,这是当时拍的片子。”他反复看了病人的所有病历和影像资料,低低的声音里一股坚定,“可能救不活了。”家属显然有点懵,一时无措,低垂了头又扬起,“就一点活下去的可能性都没有了吗?上呼吸机呢?”曹勇依旧低低的声调:“应该是救不回来了,病人自己的呼吸已经没有了,双侧瞳孔散大了,再上几个星期的呼吸机可能没有意义,对病人来说也是痛苦。”门诊里开始沉默,短暂的沉默。
他的直接,让家属颇有些吃不消,其中一位已经开始小声啜泣起来。家属离开后,他淡淡的语气,“很少能有医生像我说得这么直接深入的吧!”继而反问一句:“你觉得他们从急诊那里没有得到相同的诊断吗?只是不愿意相信而已,决心难下。其实,他们缺的就是一个帮他们做决定的人。”
1995年,曹勇首都医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
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素来有转科的传统,新来的毕业生总要经历这个过程再决定留在哪个病区。曹勇最初是在神外七病区,副主任吴震带他。在吴震眼里,曹勇是个做事认真、勤于思考、爱读书以及接受力特别强的人。“他很安静,爱琢磨,说什么一点就通,而且有中国文人身上的儒雅气质。”
两年的磨砺,成为他医生职业生涯里过渡的一环,他庆幸自己遇到了良师益友,逐渐在工作中找到节奏,自言“非常充实的两年”。
1997年,他开始硕博连读,导师是赵继宗院士。他提到赵院士,话语间很是推崇,“赵院士勤于思考,善于学习。即使对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比如讲话发言的学问也在日常中不断总结反省,力求完美。”赵院士讲话逻辑性强,思路层次清晰,没有废话,他深恶痛绝说话不断插入“然后”。
多日的跟访中,都能感受到曹勇的回答亦竭力拒绝废话,强调逻辑性。老师的言传身教如春风化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曹勇说,赵院士就有一种榜样的力量,传递在自己身上。做手术,充分准备,如果还是回天乏术,他亦心内坦然,“我尽力了,没有遗憾”。
已故的王忠诚院士提出,他的继任者应该继续发展中国神经外科事业,使中国神经外科在世界上拥有相称的大国地位。曹勇认为“中国神经外科正在奔向这一目标的大路上”。
在赵院士的帮助下,2006年,曹勇于美国BARROW神经学研究所访问学习。在这期间,他更加感受到了中国神经外科与国外发达国家神经外科的差距及治疗理念的不同。
在曹勇看来,临床大夫除了做好专业,也要做一个科学家。他对自己的定位,“Becomeascientistsurgeon”。
曹勇表示,实验室的工作,更多地是在培养一个临床大夫的科研思维,“有没有科研思维对一位大夫以后的发展很有影响”。所以,他带硕士博士学生,一定会要求他们至少有半年时间在实验室里做研究。
在他的观念里,即便是县医院的大夫,也可以做科学研究。“美国的小学生都可以提出问题,家里有人得胰腺癌死了,就会想怎么才能快速诊断胰腺癌,最后研究出可以通过一滴血就能快速诊断出胰腺癌,还因此获奖。”重点是有没有科研意识,勤于思考很必要,“如果只是反复做手术而没有思考,那只是在模仿,没有突破。病例积累到一定数量,自然会有所思考、比对和发现”。
当初,王忠诚院士创立北京神经外科研究所,也是要把临床工作中发现的问题与基础研究结合起来,通过研究更好地应用于临床治疗。曹勇说,“这是相得益彰的事情”。医学进步就是在这样的点滴摸索之中显现的。在临床和科研之间,曹勇也苦恼,“我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平衡点不好找”。
“现在我的科研和手术的分配是三七开,我所希望的是能达到五五开,可以多一些时间做科研。”
手术室里,他安静的做手术,很少说话。
在曹勇看来,年龄越大,越要勤于思考,专注临床工作没错,但是要鼓励医生去做科研,学习新知识。曹勇今年45岁,正是外科大夫的黄金时期。岁月留下的痕迹已被他悄然吸收,更多的是内化的气质。
“有多少问题是出在简单的小手术上?”他看似云淡风轻地诘问。技术很重要,但是做手术还是要用心。有业内人士称拒作手术匠,他直言,只有手术技艺十分高超的人才能说这样的话吧,若连技术都不过关,又有什么资格置喙。其实先做一名合格的手术匠就已不易,把技术练好再考虑其他。
手术技术的提升从来不是一蹴而就,方方面面怎么处理都是经验累积出来的。“比如动静脉出血的止血,很困难,所以要把电量调低一点,电灼时连带一点周围的组织。”每个外科大夫都会经历这些阶段,他们也都花了近十年的时间提升技艺,但又深知,这是一辈子的事业。
他呈现了太多的面相,成熟的,低调的,深沉的,内敛的,而同时又有与这些背道而驰的。
吴震打趣他:“曹勇笑起来的时候很阳光,像邻家大男孩!”曹勇也笑着还击:“吴主任更像!”
他们关系好,2013~2014年,曹勇在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博士后学习。期间,吴震带了一帮朋友去看他。“那时候真是挺感动的,一个人在异国他乡,见到老师格外亲切。”
旧金山的学习生活,让他对这座城市也产生了感情。2013年2月2号,他正式开通了微信发了第一条朋友圈——“窗外的天空”,用以记录旧金山的学习生活。“我去过美国很多地方,特别喜欢旧金山。”他脸上溢满了快乐,一一细数着那里的美好——“温度适宜,风景怡人,长长的海岸线,日落的时候,看着太阳就掉到海里了,彩霞满天。”
他说,UCSF有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拥有很多优秀的科学家和医生。“他们那里四季如春,夏天也凉飕飕,不像北京热得要命。你想平均每年能多出来两个月时间学习工作,能不得诺贝尔奖嘛?”学校牛人很多,和他们聊天讨论,一些原本糊里糊涂的事情渐渐清晰起来,也知道我们差在哪儿了。
记者手记
相较于被宣传报道,曹勇更喜欢自己成为执笔者,觉得写写东西挺好,“如果我去参加一个会,把所听所想写出来,大家分享有多好。”对于医学科普,则尤其较真,“最好还是医学专业的人来写,其中逻辑关系恐怕非专业人士不能够叙述清楚。”
与很多大夫不同的是,他微信朋友圈的使用率不低,所发表见解评论亦颇有独特处。订阅号则多是关乎历史,他看后唏嘘,并不是每期推送文章都好。因为忙,书店也不常去了,参加的会越来越多。他喜欢阅读,喜欢王小波,因其文字凝练,富于节奏,逻辑性强;
他喜欢长跑,像阿甘那样,不问因由,于其中获得愉悦,感受着四季变换,人世流转。他做手术,数量之外更追求质量,技术打底,复盘为盖,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他常援引一位前辈的话,“当你做了10例同类手术,觉得自己什么都行;当你做到100例的时候,才发现自己什么都不行。”到今日,他说,自己尚未达到手术匠的级别,路,还很长。
解毒,消肿,止痛。临床主要用于中、晚期肿瘤的治疗,亦可用于慢性乙型肝炎等症。
健客价: ¥280本品为非甾体抗炎药。临床可用于抗血栓:本品对血小板聚集有抑制作用,可防止血栓形成,临床用于预防一过性脑缺血发作、心肌梗死、心房颤动、人工心脏瓣膜、动静脉瘘或其他手术后的血栓形成。也可用于治疗不稳定型心绞痛。
健客价: ¥7.7抗胆碱药,临床主要用于解除平滑肌痉挛、胃肠绞痛、胆道痉挛以及有机磷中毒等。
健客价: ¥13临床用于慢性迁延性肝炎伴ALT升高者,也可用于化学毒性、药物引起ALT升高。
健客价: ¥20.9临床用于慢性鼻炎、急慢性咽喉炎、口腔溃疡、水痘、带状疱疹和扁平疣等。
健客价: ¥11补肝肾,益气活血。用于乙型肝炎,辨证属于肝肾两虚证候。临床表现为: 肝区隐痛不适,全身乏力,腰膝酸软,气短心悸,自汗,头晕,纳少,舌淡,脉弱。
健客价: ¥17.9在决定使用本品前,应仔细考虑本品和其他治疗选择的潜在利益和风险。根据每例患者的治疗目标,在最短治疗时间内使用最低有效剂量(见[注意事项]-警告)。 (1)用于缓解骨关节炎的症状和体征。 (2)用于缓解成人类风湿关节炎的症状和体征。 (3)用于治疗成人急性疼痛。(见[临床试验])
健客价: ¥39奥氮平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 初始治疗有效的患者,奥氮平在维持治疗期间能够保持基临床效果。 奥氮平用于治疗、重度躁狂发作。 对奥氮平治疗有效的躁狂发作患者,奥氮平可用于预防双相情感障碍的复发。
健客价: ¥632奥氮平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初始治疗有效的患者,奥氮平在维持治疗期间能够保持基临床效果。奥氮平用于治疗、重度躁狂发作。对奥氮平治疗有效的躁狂发作患者,奥氮平可用于预防双相情感障碍的复发。
健客价: ¥103抗胆碱药,临床主要用于解除平滑肌痉挛、胃肠绞痛、胆道痉挛以及有机磷中毒等。
健客价: ¥18临床适用于慢性鼻炎、急慢性咽喉炎、口腔溃疡、水痘、带状疱疹和扁平疣等。
健客价: ¥16临床用于慢性鼻炎、急慢性咽喉炎、口腔溃疡、水痘.带状疱疹和扁平疣等。
健客价: ¥6.25临床用于慢性迁延肝炎伴ALT升高者,也可用于化学毒物、药物引起的ALT升高。
健客价: ¥22益气活血,通络止痛。用于治疗糖尿病性周围神经病变属气虚络阻证,临床表现为四肢末梢及躯干部麻木、疼痛及感觉异常;或见肌肤甲错、面色晦暗、倦怠乏力、神疲懒言、自汗等。
健客价: ¥160适用于绝经后妇女的晚期乳腺癌的治疗。对雌激素受体阴性的病人,若其对他莫昔芬呈现阳性的临床反应,可考虑使用本品。 适用于绝经后妇女雌激素受体阳性的早期乳腺癌的辅助治疗。
健客价: ¥160奥氮平适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 对奥氮平初次治疗有效的患者,巩固治疗可以有效维持临床症状改善。 奥氮平适用于治疗中到重度的躁狂发作。 对奥氮平治疗有效的躁狂发作患者,奥氮平可以预防双相情感障碍的复发。
健客价: ¥399补肝肾,益气活血。用于乙型肝炎,辨证属于肝肾两虚证候。临床表现为:肝区隐痛不适,全身乏力,腰膝酸软,气短心悸,自汗,头晕、纳少,舌淡脉弱。
健客价: ¥20奥氮平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初始治疗有效的患者,奥氮平在维持治疗期间能够保持基临床效果。奥氮平用于治疗、重度躁狂发作。对奥氮平治疗有效的躁狂发作患者,奥氮平可用于预防双相情感障碍的复发。
健客价: ¥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