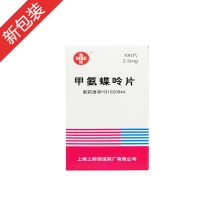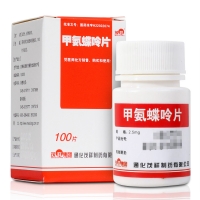2018年,随着O药和K药相继在中国获批上市,中国的资本和药企对靶向PD-1/PD-L1的免疫治疗的热情达到了巅峰,大量的药企在开展相关的临床研究,一度出现没有足够的医生和患者参与临床研究的局面。
火热的另一面是,虽然PD-1抗体对实体瘤表现出良好的疗效,但是当面对每个独立的癌症患者时,没有任何一个科学家或医生能确定PD-1抗体对这个患者是否有效。
1943年,当LudwikGross博士将小鼠身上的肿瘤切除,再把相同的癌细胞移植到同一只小鼠身上之后,他意外地发现小鼠竟然没有再长出肿瘤[1]。
也就是在那个时间点,很多科学家意识到免疫系统应该可以识别癌细胞,并杀死它。借助免疫系统治疗癌症的种子在那一刻埋在了科学家的心中。
在随后的50多年里,科学家在免疫细胞表面上发现了识别抗原的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分子[2],在癌细胞表面发现了许多因基因突变产生的新抗原[3-8]。
免疫细胞识别癌细胞的秘密被揭开了。
处于世纪之交的2000年,参与CTLA-4抗体研发的医生和科学家,在转移性黑色素瘤患者身上,首次见证了免疫抑制解除后,免疫细胞识别并杀死癌细胞的强大威力。
不过,这种效果能否在其他癌种中复现,当时科学家并不确定。因为在那时,是不是所有的癌种都携带有能被免疫细胞识别的新抗原,以及携带多少还是未知数。
好在基因测序技术的成熟,帮助科学家解答了上述问题。
2007年,在11家顶级研究机构的通力合作下,肠癌和乳腺癌的全外显子测序数据发布[9]。2008年,首份肿瘤全基因组测序数据发布[10]。
同年,肿瘤学领域两位鼎鼎大名的科学家JamesAllison和BertVogelstein带队,将乳腺癌和结直肠癌的测序数据用寻找新抗原的算法分析,在乳腺癌和肠癌组织中发现大量的新抗原[11]。于是他们提出,由于癌细胞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积累新的突变,因此所有的癌症都有可能形成免疫系统能识别的新抗原。
随后大量研究证明,大量的癌种携带基因突变带来的新抗原[12]。如此看来免疫治疗大有可为。
2010年,FDA批准首个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pilimumab用于治疗黑色素瘤[13]。
4年之后,PD-1抗体nivolumab和pembrolizumab先后上市,彻底给癌症的治疗打开了另一扇大门。
这是人类抗癌史上重要的里程碑事件,也是人类抗癌技术升级的重要转折点。
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不过一切并没有那么容易。
虽然CTLA-4抗体和PD-1抗体显示出了良好的抗癌效果,但是当此之时,由于缺少有效的患者筛选手段,导致从治疗中获益的患者占比非常低。
尽管一些研究已经确定了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抗癌效果与外周血淋巴细胞计数,T细胞活化标志物[14],“炎症”微环境[15,16]和维持高频的T细胞受体克隆型[17]之间有相关性。
不过,这些方法的筛选效果并不能令人满意。故而,患者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治疗中获益的分子决定因素究竟是啥?这个问题迫在眉睫。
在搞清楚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得看看在免疫治疗的过程中,抗肿瘤的T细胞和癌细胞如何做到“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首先,“打铁还需身子硬”,T细胞要想杀癌细胞,自己必须得活跃起来;要不然,T细胞就压根没有狙击癌细胞的能力。其次,一个“欠揍”的癌细胞必须得有足够撩T细胞的新抗原;如果新抗原不足,T细胞就极有可能认为面前的癌细胞是某个正常细胞在偶尔使坏,就对它视而不见了。
也就是说,在实际应用中,我们可以从T细胞的活性和癌细胞的免疫原性(新抗原),这两个角度去预测免疫治疗的效果。
先从T细胞的活性说起。我们都知道癌细胞通过表达PD-1的受体PD-L1抑制T细胞的活性。而且科学家也在许多不同的肿瘤组织中发现PD-L1高表达,而且与患者的预后差有关。而且研究人员也在多个PD-1抗体的临床研究中注意到,治疗前肿瘤组织中的PD-L1水平与治疗的效果有关[18,19]。后来前瞻性的临床研究也证实,肿瘤组织中PD-L1的表达水平确实是预测PD-1抗体治疗效果的标志物[20]。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2015年10月2日,FDA批准pembrolizumab治疗晚期(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NSCLC)时,首次将PD-L1的表达水平作为标志物。随后,PD-1抗体的很多适应症获批,都将PD-L1的表达水平作为一个治疗标准。
不过遗憾的是,PD-L1的表达水平也不能总是奏效,背后的原因也鲜为人知。不过,此时或许可以转而考虑癌细胞表面的新抗原。
通常来讲,癌细胞的新抗原是基因突变导致的。癌细胞获得突变的方式有很多,例如紫外线、辐射、香烟烟雾等物理和化学方式会导致体细胞突变;DNA复制或DNA错配修复路径缺陷(mismatchrepairdeficient,dMMR)会导致基因组的不稳定,致使突变积累或出现微卫星不稳定(Microsatelliteinstability,MSI)。
2013年,EvanJ.Lipson等用PD-1抗体pembrolizumab开展的一个研究让他们意识到:PD-1抗体对携带dMMR的癌症患者可能更有效[21]。
2015年,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癌症学家LuisAlbertoDiaz,Jr.团队通过一项前瞻性研究[22],证实了EvanJ.Lipson的猜想。在dMMR肠癌患者中,免疫治疗的客观响应率是40%,无进展生存率是78%;而在没有dMMR肠癌患者中,客观响应率是0%,无进展生存率是11%。这个研究表明,dMMR可以作为PD-1抗体疗效预测指标。
2017年,pembrolizumab和nivolumab先后获批用于治疗携带dMMR的癌症患者。
尽管PD-L1和dMMR的检测都获得了FDA的批准,实际上它们都有自身的不足。
以PD-L1免疫组化作为生物标志物存在一些缺陷[23]:采用细针穿刺活检等获得的小活检样本可能漏检某些肿瘤;患者个体的PD-L1表达水平可随时间的推移或解剖部位的不同而发生改变;既往治疗可能改变PD-L1的表达;某些抗体检测PD-L1表位可能不稳定;用于检测PD-L1的抗体具有不同的亲和力和特异性;PD-L1可表达于肿瘤微环境内的多种细胞类型。
各种检测方法判定的PD-L1水平不一致率高达50%[24]。此外,有研究表明,PD-1/PD-L1检测的假阳性高达42%,假阴性高达28%[25]。
对于dMMR而言,我们可以看看它在各种不同的癌种中的携带比例[26]。
显然,我们还需要其他更有代表性的标志物。其实,从免疫治疗开始进入临床阶段的时候,科学家就在寻找。
有赖于基因测序技术的进步,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MSKCC)的JeddD.Wolchok和TimothyA.Chan领导的研究团队,尝试从肿瘤基因组学的角度回顾性地探索这一重要问题。
既然免疫治疗是否有抗癌效果,主要依赖于免疫细胞对癌细胞特异性抗原的识别;那么,从理论上讲,那些携带基因突变越多的癌症患者,癌细胞产生的新抗原越多,被免疫细胞识别的可能性更高。也就是说,肿瘤组织的突变负荷(tumormutationalburden,TMB)越高,患者或许从免疫治疗中获益越多。
2014年,通过分析接受过CTLA-4抗体治疗癌症患者的全外显子(WES)测序数据,研究人员研究了TMB与治疗效果之间的关系[27]。
很幸运,他们发现了TMB与免疫治疗效果之间的关系,但是遗憾的是单独依赖肿瘤突变负荷,不足以预测患者的预后。这个研究也证实了,一直以来被认为对癌症的发展方向没左右能力的“乘客突变”,极有可能是肿瘤是否响应免疫治疗的“免疫决定因素”这一假说。也为用外显子测序指导免疫治疗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也是TMB首次邂逅免疫治疗。
伴随着2014年下半年,两款PD-1抗体分别获得FDA的上市批准。TimothyA.Chan又带领研究团队分析了肿瘤突变与PD-1抗体治疗响应之间的关系。
不出意外,在两个队列的回顾性研究中,再次借助全外显子测序(WES),TimothyA.Chan发现,在接受PD-1抗体治疗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肿瘤中较高的非同义突变负担与客观反应提升,持久的临床益处和无进展存活相关。2015年初,这项临床回顾性研究结果发表在《科学》上[28]。
在TMB走向巅峰的过程中,最让人震惊的事件发生在前两年。
2016年,施贵宝(BMS)宣布其PD-1抗体nivolumab在非小细胞肺癌III期临床Checkmate-026中没有抵达主要临床终点[29]。对于那些PD-L1≥5%,且未经治疗的晚期肺癌患者,nivolumab未能比标准化疗延长无进展生存期。
按照之前对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理解,PD-L1≥5%疗效还不好,这是难以置信的。不过它发生了,事实就摆在那里。研究人员认为,Checkmate-026失败的锅,不能让nivolumab背,背后肯定有其他原因。
于是他们又回过头去分析试验数据,发现TMB水平高的患者,用nivolumab进行治疗后,肿瘤缓解和生存获益的结果都显著优于化疗[30]。
TMB这才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上面的两个回顾性研究表明,TMB可能是预测免疫治疗效果的优秀标志物。不过,如果是用全外显子测序评估肿瘤组织的TMB,这个成本恐怕会高的没人用的起。所以,这两个研究也没有引起太大的轰动效应。
FoundationMedicine,Inc(FMI)和MSKCC的努力让事情出现了转机。
其中FMI推出了FoundationOne(F1),这款产品分析数百个癌症相关基因的总计约1.1Mb大小的外显子序列,然后计算TMB水平。
大量的研究表明,以F1为代表的TMB检测与WES相比,一致性高[31-33]。
2017年,FMI发布了接受F1检测的10万例患者数据分析[34]。数据显示,通过F1评估的TMB与全外显子(WES)测序一样准确。
此外,这个研究还全面评估了百余种癌症的TMB图谱,分析了TMB与MSI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83%的MSI-H同时也是TMB-H,且97%的MSI-H样本的TMB≥10mut/Mb;只有16%的TMB-H样本同时为MSI-H。这也意味着,TMB可能比dMMR和MSI使用范围更广。
同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ElizabethMarionJaffee教授在分析了多个临床研究数据之后,得出结论[35]:TMB对27种肿瘤类型的免疫治疗有显著的预测作?,TMB与ORR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P<0.001),相关系数为0.74,这意味着在这27种肿瘤中,55%的ORR差异可以用TMB来解释;凸显了TMB与抗PD-1治疗疗效之间存在强相关性。
基于前期的一系列高质量研究,FDA最终批准了FoundationOneCDx成为首个泛瘤种伴随诊断产品,它覆盖了324个基因,两个预测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疗效的分子标记MSI和TMB(TMB计算方法:0.8Mb编码区域里包含所有的同义突变和非同义突变,并去掉胚系突变和肿瘤驱动突变),覆盖全部实体瘤(除肉瘤)。
到了2018年,证明TMB实力的前瞻性研究论文终于发表。
这项在非小细胞肺癌中开展的的临床研究(CheckMate-227),使用了FMI的伴随诊断产品FoundationOneCDx。结果表明:在TMB≥10mut/Mb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与铂类双联化疗相比,nivolumab加低剂量ipilimumab治疗明显延长了1年的无进展生存率(42.6%vs13.2%),翻了3倍多;无进展生存期也显著延长(7.2月vs5.4月)[36]。
在刚刚闭幕的2018年欧洲肿瘤医学协会会议(ESMO)上,FMI的科学家又系统地分析了FoundationOneCDx计算的TMB与全外显子检测的匹配度。研究人员再次证实,只要临床组织样本中肿瘤细胞的含量能达到20%,FoundationOneCDx计算的TMB就能达到非常好的可重复性,可重现性,灵敏性和准确性。
这个研究结果是在全球范围内首次在III期临床试验中证实:无论PD-L1表达水平如何,只要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TMB高,联合免疫治疗都能够给他们带来无进展生存期显著获益。也是首个证实TMB可以作为免疫治疗效果预测伴随诊断方法的前瞻性临床研究。
与此同时,另一项并列开展中的CheckMate568也表明,在接受nivolumab加ipilimumab治疗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TMB≥10mut/Mb的患者中位无进展生存期几乎是TMB<10mut/Mb患者的3倍(7.1月vs2.6月),无论PD-L1表达水平如何。
这两个研究奠定了TMB在预测免疫治疗效果中的地位。
正是基于这些研究成果,在今年刚刚推出的非小细胞肺癌NCCN指南中,TMB赫然在列,成为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接受免疫治疗的推荐检测方法。
尽管如此,TMB仍面临一些问题。从前面的临床研究中我们也不难看出,有些TMB非常高的患者对免疫治疗也没有反应,有些TMB低的患者使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效果却很好。
这意味着,除了TMB之外,患者对免疫治疗的响应程度还与其他多种因素有关。这也提示,将TMB与其他的标志物联合使用可能会提升TMB的预测能力。
近日,RazvanCristescu等在《科学》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给了我们一定的启示:同时检测T细胞的活性水平和TMB可能是个不错的方向[37]。
此外,目前TMB检测主要还是基于肿瘤组织。然而,有很多患者没有足够的肿瘤组织可供使用,甚至有些患者还不适合做组织活检,在非小细胞肺癌里面就有近30%的患者是这样的状况[38,39]。
日前,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综合癌症中心、基因泰克公司和FMI联合证实,血浆中肿瘤突变负荷(bTMB)可准确重复测量,并且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疗效相关。证实了bTMB对免疫治疗药物疗效预测的有效性[40]。
就在这个研究发表的数日后,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华人学者XuXiaowei和GuoWei发现,肿瘤内的癌细胞会产生携带压制T细胞活性的PD-L1的外泌体,这种外泌体从肿瘤组织中直接散播到全身各处,对人体的免疫系统进行全面的打击和压制[41]。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医生可以直接从癌症患者身上抽一管血,就可以评估T细胞的活性和癌细胞的免疫原性,最终实现准确的判断患者对免疫治疗的反应。
主要治疗消化道肿瘤,对胃癌、结肠癌、直肠癌有一定疗效。也可用于治疗乳腺癌、支气管肺癌和肝癌等。还可用于膀胱癌、前列腺癌、肾癌等。
健客价: ¥401、各型急性白血病,特别是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恶性淋巴瘤、非何杰金氏淋巴瘤和蕈样肉芽肿、多发性骨髓病。2、头颈部癌、肺癌、各种软组织肉瘤、银屑病。3、乳腺癌、卵巢癌、宫颈癌、恶性葡萄胎、绒毛膜上皮癌、
健客价: ¥1391.各型急性白血病,特别是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恶性淋巴瘤、非何杰金氏淋巴瘤和蕈样肉芽肿、多发性骨髓病; 2.头颈部癌、肺癌、各种软组织肉瘤、银屑病; 3.乳腺癌、卵巢癌、宫颈癌、恶性葡萄胎、绒毛膜上皮癌、睾丸癌。
健客价: ¥102破血消瘦,攻毒蚀疮。用于原发性肝癌、肺癌、直肠癌、恶性淋巴瘤、妇科恶性肿瘤等。
健客价: ¥32扶正固本,活血消症。适用于正气虚弱,瘀血阻滞,原发性肝癌不宜手术和化疗者辅助治疗用药,有改善肝区疼痛、腹胀、乏力等症状的作用。在标准的化学药品抗癌治疗的基础上,可用于肺癌、胃肠癌、乳腺癌所致的神疲乏力、少气懒言、脘腹疼痛或胀闷、纳谷少馨、大便干结或溏泄、或气促、咳嗽、多痰、面色晄白、胸胁不适等症,改善患者生活质量。
健客价: ¥115抗癌药。用于肺癌、肺癌脑转移,消化道肿瘤及肝癌的辅助治疗。
健客价: ¥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