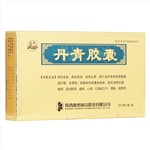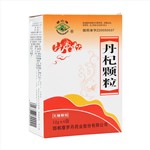我有一个出版界的朋友,是那种热爱户外运动、保持着健康体魄和肤色的男人。他来看望我的那天,我正走在湖畔小路上,全身沐浴在午后的阳光里。他注视着我——他心目中一个病入膏肓的人,上下打量,眼睛里迅速聚起难以置信的神情。“你怎么一点也不像个病人?”他说,同时挥舞了一下紧绷在短袖T恤衫里的胳膊,伸到我面前,“看看你,晒得比我还黑。”这是一个烈日炎炎的夏天,周围树木郁郁葱葱,天气酷热难耐。周围游人稀少,仅有的几位也都躲在凉亭里,我却特意挑选了一处没有树荫的石凳坐下。阳光从头顶洒下来,明亮异常,把我们的身影投在地上,线条清晰。泥土路面在我们脚下散发着太阳的炽热。我俩一同把胳膊举起来,迎接灿烂的阳光。我的皮肤看上去黑里透红,似乎很接近小说家笔下的那种古铜色。
我的这位朋友有个先入为主的印象:癌症病人应该是面色苍白,躺在床上,气若游丝,淹没在一片昏暗的气息中。不料,他眼前这个人竟和想象中完全不同。
他望着我,还有我身上炽热的光芒,迷惑不解。我告诉他,这几年来,我一直在一丝不苟地执行一项计划:日光浴。不是追求什么健美的肤色,而是希望自己的身体拥有更强大的力量去抵御疾病。
我的“日光浴”是不分酷暑寒冬的,也可以说是“冬晒三九,夏晒三伏”。冬日里外面天寒地冻,我在室内靠窗的地方席地而坐,赤裸上身,让阳光直接照在我的皮肤上,同时透过玻璃窗欣赏外面的冰天雪地。
等到春天来临,天气转暖,我就可以坐在室外朝南的露台上,悉心体会乡下老汉背靠南墙晒太阳的乐趣。夏天原本是个酷热难耐的时节,现在却成了我的黄金季节——其实对我来说,没有哪个季节不是黄金季节,因为我可以让自己的大部分皮肤暴露在阳光下。我通常只穿一条短裤,旁若无人地漫步在小路上,同时刻意地绕开树冠林荫。
随着炽热的空气吞噬整个城市,街头和广场变得沉闷无声。路人行色匆匆,走在高楼的阴影里,躲避着烈日,就连处处绿荫的公园也杳无人影,一向悠闲自在的游人全都不见了踪影,只剩下几位不怕酷暑的老人坐在树荫下纳凉,一边远远地用目光追着我。在这些知冷知热的人看来,我的行为真是太古怪了。癌症患者最困难的一件事就是户外活动。有一段时间,我感觉自己也逃不过同样的命运了。运动原本是我的爱好,比如游泳、登山和滑雪,此外我每天还在健身房里度过大约一个小时。可是在疾病猝然降临的日子里,这一切都不行了。我无法再走到户外去享受一下人在天地间的感觉。
那时候,我最担心的事情甚至不是我体内的肿瘤细胞,而是不得不像只老鼠一样整天躲在昏暗角落,遵循着一种消沉萎靡的节奏,没有蓝天白云,没有风雨雪雾,也没有阳光。想到即使是一个健康人,过这样的生活也会完蛋,我不禁一阵沮丧。那些天,家里气氛低沉,亲友的看望和问候也特别多。每天都会带来一些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好消息——不是哪位癌症患者延年益寿的故事,就是在什么地方又有了一种什么“
抗癌新药”。每个人都想逗我开心,可是我反应迟钝。因为我知道,癌症患者的康复之路上,坏消息总是绵绵不绝,而好消息通常都会言过其实。
直到有一天,我接到妹妹从欧洲打来的电话。她劝我尽可能走到户外去晒太阳。“体内维生素D的水平对于肿瘤患者的生存至关重要。”她解释说,“尤其是肺癌患者。”而晒太阳正是提高体内维生素D水平的最佳途径。她的声音里充满了乐观的调子。我完全可以想象电话那头她的样子。她对于这类消息一向抱着怀疑态度。这一回,不会是让谁给忽悠了吧?我这样想时,一定是流露出什么情绪传递到电话那头。“你最好试试,”她不屈不挠地说,“至少没什么坏处。”为了让我对这个建议给予足够的关注,她又给我发来电子邮件,附带了一份医学研究的报道。
我从中第一次知道,“补充维生素D和晒太阳,能延长早期肺癌患者的术后存活时间”。阳光与肺癌患者康复具有相关性的结论,来自美国哈佛医学院和公共卫生学院联合开展的一项研究。
我们已经知道,早期肺癌患者在手术之后的“五年存活率”为60%。这是一个平均数,具体到每个人就很不一样,有的长些,有的短些。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一定是有原因的,可惜一直没有人能够解释清楚。现在,哈佛医学院和公共卫生学院的这项研究指出,体内维生素D的水平对于肿瘤患者的生存至关重要。研究者抽取1992年至2000年接受治疗的456位早期肺癌患者的病历,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发现,同维生素D水平低、手术后晒太阳少的人相比,维生素D水平高、晒太阳多的患者术后“五年存活率”能够明显提高。在一项公开发表的研究报告中,专家们进一步指出,根据“五年存活率”这一分界点,维生素D摄入量高的患者“五年存活率”为72%,而维生素D摄入量低的患者“五年存活率”仅为29%。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只要多晒太阳,肺癌患者就有可能把手术后平均的“五年存活率”提高12个百分点——从60%提高到72%!相反,待在昏暗的房间里,终日不见阳光,就有可能把“五年存活率”降低31个百分点——从60%降低到29%。这结论立刻触动了我。因为在我手术之后,一位肿瘤专家在谈及化疗的效果时曾告诉我,化疗能让我的术后“五年存活率”提高两个百分点——从60%提高到62%。
换句话说,在防止癌细胞复发、扩散和转移方面,坚持“日光浴”和补充维生素D所能获得的正面效果,有可能相当于化疗的6倍。而且还有更重要的:它没有什么副作用,也不花钱。这一研究结论真的能够成立吗?维生素D为什么有助于患者抵御癌细胞的侵蚀?晒太阳和这些又有什么关系?这些问题对我的意义显然非同寻常,也激起了我的好奇心。随后的几天,我把注意力转向搜寻关于维生素D的更多资料,像个初入医学院的年轻学生一样满怀热情。我很快就了解到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原来,维生素D是一种固醇类衍生物。它通常被用来调节体内钙、磷代谢和平衡,以维持
骨骼健康。近几年,欧美国家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维生素D还具有另外一些奇特的功能,其中之一就是“预防慢性代谢性疾病”。在许多专家看来,肿瘤细胞的滋生、突变和暴发,在本质上正是一种“代谢性疾病”。有一种理论认为,每个人体内都存在癌细胞,每个人生活的环境都存在着诱使正常细胞癌变的物质,只是外界的致癌因素不同,自身代谢废弃物的能力也不同,这决定了肿瘤会不会发生、什么时候发生。当体内某一部分的代谢功能和免疫力相对较差时,身体代谢的废弃物便会聚集在那里,导致正常细胞变异,进而形成肿瘤。所谓“癌细胞的转移”,也是肌体废弃物不断寻找自我净化能力薄弱的部位,并重新集结的过程。一位名叫孙传正的中国医生,正是依据这种理论,把癌症叫作“全身性代谢废物稽留综合征”。另外一个美国人,柯林·坎贝尔博士,在他的一本影响巨大的书中,阐述了维生素D及其代谢产物对几种疾病的影响,以及人体细胞的反应机制。与此同时,这位国际著名的营养学家,令人信服地把“晒太阳”和“补充维生素D”联系在一起。他解释说,“阳光中的紫外线能将皮肤中的维生素D前体物转化成维生素D”,输送到肝脏里,被某种酶转化为一种维生素D代谢产物。此后,在一个相当关键的步骤中,肝脏存储形式的维生素D被输入肾脏,并在肾脏中被另一种酶转化为维生素D的活化代谢物,叫作钙三醇。
然后,我们便得到了真正需要的东西:钙三醇形式的维生素D。它“可以遏制健康组织向病态组织的转变”。(详见T.柯林·坎贝尔、托马斯·M.坎贝尔所著《中国健康调查报告》,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我猜想,缺乏维生素D不会是导致疾病的唯一因素,但是,维生素D的重要性也是可信的。
此外还有一件事应当搞清楚:我们中国人血液中维生素D的整体水平远远低于正常标准,而以中老年人群更甚。根据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营养科学研究所的一项研究,我国中老年人群中,有93.6%的人体内维生素D低于正常值(其中69.2%缺乏维生素D,另外24.4%则属于“不足”),而维生素D充足的个体仅占6.4%。我怎么也没料到会看到这样一种局面,于是迫切地想知道自己体内维生素D的水平。我开始寻找医院,希望能够做一次检查。令人惊讶的是,北京的几家大医院居然都没有这项检查。我托朋友到上海去打听,竟也没有。万般无奈,我只好自己来做大致的估算。回想自己的生活习惯,虽然喜欢吃鱼,却是淡水鱼多,深海鱼少;虽然喜欢运动,却是室内运动多,户外运动少。看来,用不着去做什么检查了。我应当属于“维生素D低于正常值”的那93.6%。接下来的问题是,我能从哪里获得维生素D呢?坏消息是,我们很难通过食物直接获得足够的维生素D。因为维生素D主要存在于深海鱼类中,这在我们中国人的食物中并不多见。而我们经常吃的东西里面,比如谷物、蔬菜和肉类,含维生素D不多。好消息是,阳光中的紫外线能在皮肤中合成维生素D。所以,只要能够多晒太阳,就能获得身体对维生素D需求量的90%以上。“如果你想知道到底通过充分的阳光来获得维生素D好,还是通过食品来补充维生素D好,”坎贝尔博士写道,“那么我告诉你,晒太阳绝对更有价值。”为了证明自己不是信口胡说,他列举出一项覆盖全球120个国家的调查,结果表明,很多慢性病的发病率,比如
糖尿病、关节炎、骨质疏松症、癌症,会随着纬度的升高而升高——越是接近北极和南极也就越常见,因为那里属于日照较少的地区。
我不禁想到,今天人们体内维生素D的匮乏,除了地理位置之外,一定还和他们的现代生活方式有关。一年四季,我们有意无意地把自己关在室内,终日不见阳光。这会不会也成为癌症发病率不断升高的一个原因呢?我猜想,在远古时代,原始人是不会缺少维生素D的。他们终日风餐露宿,日晒雨淋,连一件能完全遮挡身体的衣服也没有。
后来,人们开始为自己搭建茅屋栖息,但仍然要在烈日下劳作——无论是狩猎还是农耕。逐渐地,由狩猎而游牧,由农耕而工业,人们给自己盖的房子越来越坚固,越来越舒适,不仅夜晚居有定所,而且白天工作也在室内。但是,至少他们从住所到工作场所的路上还是要露天行走的。直到有一天,人类又为自己发明了“行走的房子”——汽车。
到如今这个时代,人们不论是睡觉还是工作、饮食还是行走、娱乐还是运动,全都躲在房子里,远离阳光。就连偶尔为之的户外散步,也要涂上厚厚的
防晒霜,再撑上一把遮阳伞。这样看来,我有必要让自己的每一天有一段时间回归原始人的生活方式——晒太阳。既然我打算把“晒太阳”作为治疗的一部分——就像大多数癌症患者通常经历的化疗和放疗一样,那么,就应当把这件事做得更加严谨和有规律性。所以,我让自己平均每天接触阳光的时间不少于40分钟,同时还须把皮肤50%以上的部分裸露在外。
事实上,即使在高楼林立的都市里,只要你愿意,也有足够的机会享受阳光。季节的转换会让日照的强度和时间发生变化,所以我也会对自己的作息时间稍做改变。一般来说,春秋季节的日照为最佳。每逢此时,我便长时间地让自己走在阳光里。盛夏骄阳似火,但是如果我在早晨9点以前和下午5点之后来到户外,就会发现阳光变得柔和可人。即使是在三九寒冬,阳光也总是比我们想象的更充沛、更温暖。当你赤身露体站到窗前,沐浴在和煦的阳光里,你会觉得好像是春天来了。
每一次走在阳光里,都是一种身体的享受,同时也是
精神的净化。我的户外作息随着阳光的变化而改变,而完全不在乎人世间的冷暖悲欢。我在这中间渐渐意识到自己的生活是多么舒适。我的体力逐渐恢复,皮肤也禁得起日晒风吹了。有人觉得光天化日之下赤身露体有失体统,有人说晒多了太阳会让人显得更加苍老,还有人提醒我过多的紫外线会诱发疾病,比如皮肤癌。我很难反驳他们,但仍然每天走在阳光里。“有失体统”也罢,“更加苍老”也罢,“诱发疾病”也罢,我都不在乎了。
自从生病以来,我还从没有感觉这样良好过。毫无疑问,这时候,治疗已经成了我的一种享受,我的生命再次被阳光照亮,生机和活力不知不觉重新回到我的身上。就算太阳并不能助我除掉肿瘤细胞,维生素D的功效也没有那么神奇,我也知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