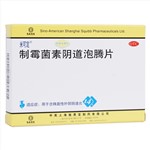【呼吸疾病研究】儿童侵袭性肺曲霉菌病16例临床分析!
摘要
目的
探讨儿童侵袭性肺曲霉菌病(IPA)的诊断及治疗。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6年1月至2014年6月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确诊或临床诊断IPA的16例患儿临床资料。四格表确切概率法进行组间比较。
结果
16例患儿中男11例,女5例,确诊1例,临床诊断15例。宿主高危因素为:长时间使用多种广谱抗菌药物16例,中性粒细胞减少症9例,有创机械通气3例,原发性免疫缺陷病2例,长期使用糖皮质激素2例,麻疹2例,先天性肺发育不良1例。16例患儿均有发热、咳嗽、咳痰(痰响)(0/7和1/7)。诊断时,中性粒细胞减少症组“晕轮征”(5/9)、胸膜下楔形实变影(7/9)高于非中性粒细胞减少症组(0/7和1/7)(P<0.05);抗曲霉菌治疗15d~1个月后,空洞、“空气新月征”阳性率高于诊断时(P<0.05)。血清半乳甘露糖聚糖抗原检测阳性率高于痰培养及血清G实验(P<0.05)。13例首选伏立康唑治疗,7例有效。
结论
中性粒细胞减少症是儿童IPA常见宿主高危因素。胸膜下楔形实变影、“晕轮征”及“空气新月征”对诊断有提示意义,前两者在有中性粒细胞减少症患儿早期更多见。血清GM实验有较高的诊断价值。大部分IPA患儿伏立康唑治疗有效。
随着临床广谱抗菌药物、糖皮质激素和抗肿瘤药物广泛应用,有创机械通气、各种导管的留置等侵入性操作的普及,骨髓移植、实体器官移植等新技术开展以及艾滋病患儿增多,儿童侵袭性肺曲霉菌病(invasivepulmonaryaspergillosis,IPA)的发病呈增高趋势。IPA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胸部CT特异性征象阳性率不高;痰检阳性率低,血清学存在假阴性,支气管镜、肺活检等侵入性检查率低,难以早期诊断。本研究对16例IPA患儿进行回顾性分析。
对象和方法
一、研究对象及诊断标准
以2006年1月至2014年6月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确诊或临床诊断IPA的16例患儿为研究对象。IPA的诊断参照2009年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呼吸学组提出的诊断标准[1];确诊:宿主高危因素+临床证据(包括临床表现+影像学征象)+肺组织病理学和(或)有确诊意义的微生物学证据;临床诊断:宿主高危因素+临床证据(包括临床表现+影像学征象)+有临床诊断意义的微生物学证据。中性粒细胞减少症的诊断参照第8版诸福棠实用儿科学[2]:≤1岁的婴儿中性粒细胞<1.0×109/L,>1岁儿童中性粒细胞<1.5×109/L。
二、方法
对16例IPA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临床资料包括患儿的性别、年龄、发病时间(出现与肺曲霉菌病相关的临床表现时间)、确定诊断时间、高危宿主因素、临床表现、典型影像学征象、实验室检查[外周血白细胞计数(WBC)、中性粒细胞计数、合格痰涂片及培养、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ronchoalveolarlavagefluid,BALF)涂片及培养、血清半乳甘露聚糖抗原检测(GM实验)、血清1,3-β-D葡聚糖抗原检测(G实验)、肺组织培养、胸腔积液培养、血培养]、组织病理学证据、治疗及预后等。
三、统计学分析
应用统计软件SPSS16.0进行分析,计数资料以构成比(%)描述,样本率的比较采用四格表的确切概率法。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一、一般资料
IPA患儿16例中男11例、女5例,男∶女为2.2∶1,发病年龄为19d至17岁10个月,其中≤1岁4例,>1~3岁4例,>3~6岁2例,>6岁6例。16例IPA患儿中确诊1例,临床诊断15例。按有无中性粒细胞减少症,将16例IPA患儿进行分组,其中中性粒细胞减少症组9例,非中性粒细胞减少症组7例。
二、宿主因素
1.中性粒细胞减少症:
中性粒细胞减少症组9例患儿,均为急性白血病化疗后。其中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8例,均为初治患儿,经长春新碱、柔红霉素、左旋门冬酰胺酶、泼尼松(VDLP)诱导方案化疗后出现骨髓抑制并发中性粒细胞减少症,诊断IPA时中性粒细胞范围0~1.18×109/L,中性粒细胞减少持续时间14~112d。另1例为急性髓细胞白血病(AML)M5b中危,经柔红霉素、阿糖胞苷、依托泊苷(DAE)巩固方案化疗后出现骨髓抑制并发中性粒细胞减少症,诊断IPA时中性粒细胞为0.02×109/L,中性粒细胞减少持续时间4d。
2.有创机械通气:
3例患儿诊断前曾分别行有创机械通气3、11、13d。
3.原发性免疫缺陷病:
2例患儿有慢性肉芽肿病(CGD)。
4.长期使用糖皮质激素:
1例患儿3岁即诊断为特发性肺含铁血黄素沉着症(IPH),给予糖皮质激素不规则治疗,至发病时间断口服醋酸泼尼松7年。1例基础疾病系统性红斑狼疮(SLE)及狼疮性肾炎(LN)Ⅲ(A)型,予大剂量甲泼尼龙15mg/(kg·d)冲击3d后,予醋酸泼尼松1mg/(kg·d)口服,至发病时已使用糖皮质激素1个月。
5.严重病毒感染:
2例患儿发病前1周患麻疹,发病时处于麻疹恢复期。
6.基础疾病:
1例患儿有先天性肺发育不良的基础疾病。
7.长期应用多种广谱抗菌药物:
16例IPA患儿诊断前均使用了2种以上广谱抗菌药物,其中最多的1例累计使用达12种。抗菌药物使用时间最短的为14d,最长的为54d。
三、临床表现
16例IPA患儿均有发热、咳嗽、咳痰(痰响);其中5例为上述症状经抗菌药物长时间治疗无好转,另11例为上述症状经抗菌药物治疗好转后重新出现。11例肺部出现中细湿啰音,10例出现气促,8例出现吸气三凹征,5例出现咯血,3例出现胸痛,2例出现喘息。
四、影像学
16例IPA患儿诊断时均行胸部CT(64排)检查。其中,最常见的影像学表现为片状高密度影,共12例,之后依次为结节或团块状实变影9例、胸膜下楔形实变影8例、“晕轮征”5例、胸膜粘连4例、胸腔积液3例、空洞2例,未见“空气新月征”。诊断IPA时,中性粒细胞减少症组患儿“晕轮征”、胸膜下楔形实变影阳性率高于非中性粒细胞减少症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余影像学表现,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体影像学特征见表1。
抗曲霉菌治疗15d至1个月内,16例IPA患儿中有9例复查了胸部CT,4例病情好转未返院复查,3例放弃治疗未复查。此期9例复查了胸部CT的IPA患儿常见的影像学表现为结节或团块状实变影、胸膜下楔形实变影、空洞,各5例;其次为胸膜粘连4例,再次为片状高密度影、“晕轮征”、“空气新月征”,各3例;而胸腔积液最少见,仅见于1例。
抗曲霉菌治疗15d至1个月内复查胸部CT,空洞及“空气新月征”的阳性率明显高于诊断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余影像学表现,诊断时与抗曲霉菌治疗15d~1个月内复查时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体比较见表2。
五、病原学检查
16例IPA患儿均进行了痰涂片、痰培养检查,其中5例痰涂片示曲霉菌,同时1周内2次痰培养示曲霉菌。2例患儿进行了支气管镜检查,并且BALF涂片及培养均阴性。12例进行了血清G实验,其中诊断前1周内2次检查均阳性者2例。10例患儿进行了血清GM实验,其中4例诊断前1周内吸光度指数连续两次均大于0.8,5例单次大于1.5。2例患儿行开胸手术治疗,并行肺组织培养,均为阴性。1例患儿行胸腔积液涂片及培养,均为阴性。16例IPA患儿前后共进行了65次血培养,均为阴性。
血清GM实验阳性率分别与痰检(痰涂片示曲霉菌及1周内2次痰培养均示曲霉菌)阳性率及血清G实验阳性率比较,血清GM实验阳性率明显高于痰检及血清G实验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六、组织病理学检查
4例患儿进行了肺活检,其中开胸肺叶切除术并肺活检1例,开胸肺楔形切除术并肺活检1例,经胸壁穿刺肺活检2例。肺组织标本部位为:右上肺叶3例,左下肺1例。4例行肺活检患儿中,1例行开胸肺叶切除术,组织病理检查示:(右上肺)真菌性肉芽肿性炎,有中性粒细胞浸润,组织纤维化,HE及PAS染色见曲霉菌丝,该例为确诊病例。1例行经胸壁穿刺肺活检,组织病理检查示:(左下肺)肺组织有不典型的上皮样细胞构成的肉芽肿,部分坏死,炎性细胞浸润,微脓肿形成;D-PAS染色疑似有阳性颗粒,肺炎并真菌感染可能性大,但切片内未见曲霉菌丝。其余病例PAS及D-PAS染色均未见曲霉菌丝或阳性颗粒。
七、治疗及预后
16例IPA患儿中,14例为单纯药物治疗,2例为药物联合外科手术治疗。14例单纯药物治疗的IPA患儿中,有1例合并粒细胞减少症的患儿首选两性霉素B静滴33d后,病情好转,再予伏立康唑片序贯口服94d后痊愈。另外13例首选伏立康唑;其中7例有效、最终痊愈的患儿中6例先予伏立康唑分别静滴3、5、7、8、17、10d,病情好转后,继予伏立康唑片序贯口服,序贯疗程分别为65、31、104、37、32、65d痊愈;1例自始至终予伏立康唑片口服,疗程3个月痊愈。3例首选伏立康唑治疗无效,最终死亡;其中2例为CGD患儿,1例为AMLM5b中危化疗患儿。3例首选伏立康唑治疗,但因并发症(2例因并发白血病肺部浸润,1例因并发中枢神经系统白血病)放弃治疗。2例药物(伏立康唑)联合外科手术治疗,有效,最终痊愈。
讨论
一、诊断
2007年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感染学组发表了“肺真菌病诊断和治疗专家共识”[3]。2008年美国感染病学会(infectiousdiseasessocietyofAmerica,IDSA)制定了“曲霉菌治疗指南”[4]。2009年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呼吸学组发表了“儿童侵袭性肺部真菌感染诊治指南”[1]。均提出了IPA的分级诊断标准,诊断依据由宿主高危因素、临床证据(包括临床表现、影像学征象)、微生物学证据(包括有临床诊断意义或确诊意义的微生学证据)及肺组织病理学4个部分组成,分为确诊、临床诊断、拟诊3个诊断级别。本研究16例患儿中1例为确诊病例,15例为临床诊断病例,确诊率低。确诊需要肺组织标本病理学检查,患儿病情危重、不能耐受、家属不接受导致肺活检开展率低;此外病变部位标本坏死不含曲霉菌,也会导致IPA确诊率低。
二、宿主高危因素
曲霉菌系条件致病菌,宿主危险因素在发病过程中起关键作用。IPA经典的危险因素是中性粒细胞减少症[5],并且持续时间及严重程度与IPA的发生密切相关。本研究16例患儿中9例存在中性粒细胞减少症,需高度警惕白血病患儿合并IPA。对于无中性粒细胞减少症的IPA,最常见的高危因素是长期使用糖皮质激素[5]。本研究7例无中性粒细胞减少症的IPA患儿,其中2例长期使用糖皮质激素。此外中性粒细胞减少症组8例ALL初治患儿,经VDLP方案诱导化疗也有较长时间使用糖皮质激素史。
相比成人,儿童IPA有其相对较为特殊的高危因素。一是原发性免疫缺陷病,尤其是联合免疫缺陷病、细胞免疫缺陷病和CGD等[1]。CGD患儿容易导致曲霉菌感染[6]。本研究中2例CGD患儿,虽予积极抗曲霉菌治疗,但最终均死亡。二是先天性肺发育异常,本组1例患儿系先天性肺发育不良。
麻疹病毒感染后可引起暂时性免疫功能低下,且在急性期后1个月开始逐渐恢复[7]。本组2例患儿在麻疹恢复期时并发IPA,予积极抗曲霉菌治疗32~37d均痊愈。
长期大量应用广谱抗菌药物,可使体内菌群失调,易导致真菌的继发感染。本研究中所有患儿在诊断IPA前均使用了至少2种以上广谱抗菌药物,但长期大量应用广谱抗菌药物能否作为IPA的单一危险因素,仍需进一步探讨研究。
三、临床表现
IPA常见症状为发热(病程中出现不能解释的高热)、咳嗽、咳痰、咯血、胸痛、呼吸困难等,均无特异性。本组16例IPA患儿均有发热、咳嗽、咳痰(痰响);其中5例上述症状经抗菌药物长时间治疗无好转,另11例上述症状经抗菌药物治疗一度好转后重新出现,提示发热、咳嗽、咳痰(痰响)经抗菌药物长时间治疗无好转或好转后重新出现可作为该病的警示信号。
四、影像学表现
本研究16例IPA患儿在诊断时,胸部CT较常见的影像学表现为片状高密度影、结节或团块状实变影,阳性率分别为75.0%、56.3%,但此两项征象对肺曲霉菌病的诊断特异性差。“胸膜下楔形实变影”、“晕轮征”在本研究IPA病例诊断时阳性率仅次于片状高密度影、结节/团块状实变影。有文献报道,“胸膜下楔形实变影”、“晕轮征”是IPA早期的特征性CT改变[8]。本研究在诊断IPA时,“胸膜下楔形实变影”、“晕轮征”在中性粒细胞减少症组阳性率,明显高于非中性粒细胞减少症组。曲霉菌喜侵袭血管,“胸膜下楔形实变影”系曲霉菌侵袭较大动脉引起出血性梗死,“晕轮征”系曲霉菌侵袭小血管导致肺实质出血性梗死[9]。中性粒细胞可杀伤曲霉菌丝,是人体内抗曲霉菌的主要免疫细胞,在抵御曲霉菌感染的过程中起关键作用。考虑中性粒细胞减少患儿中曲霉菌侵袭性更强,侵袭血管后导致“胸膜下楔形实变影”、“晕轮征”形成的几率更高。因而,“胸膜下楔形实变影”、“晕轮征”对于中性粒细胞减少症IPA患儿的早期诊断具有提示意义。“空气新月征”为IPA较特征性的CT改变,通常于侵袭性肺曲霉菌感染后8~28d出现[10]。本研究,16例IPA诊断时胸部CT均未显示“空气新月征”,治疗15d~1个月内有9例复查胸部CT,其中3例可见“空气新月征”,阳性率不高,这与陈玉玲等[11]的报道相符。
五、微生物学检查
本研究血清GM实验阳性率分别与痰检阳性率(痰涂片示曲霉菌及1周内2次痰培养均示曲霉菌)及血清G实验阳性率比较,血清GM实验阳性率明显高于痰检及血清G实验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血清GM实验相对于痰检、血清G实验对IPA诊断的灵敏度更高。GM实验是一种非侵入性诊断方法,有助于IPA的早期诊断。Klont等[12]报道在IPA出现明显的临床症状和体征之前中位时间5~8d(范围1~27d)检测到血清GM。但在临床上GM实验易出现假阴性或假阳性。假阴性结果可能与判断阳性结果的界值点有关。本研究为了提高特异度,降低误诊率,界值点的选择参照了国内张晓艳等的观点[13],吸光度指数以双次大于0.8,单次大于1.5作为阳性界值点。也符合我国儿童指南[1]。降低了灵敏度,增加了漏诊率,也是阳性病例数较少的原因之一。在实际临床工作中,针对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患儿,建议采纳2014年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血液学组制定的诊疗建议[14],吸光度指数以0.5作为阳性界值点可减少IPA漏诊率,避免错失治疗机会。Marr等[15]报道经抗真菌治疗的侵袭性曲霉菌病患者血清GM实验灵敏度下降,可出现假阴性。本研究10例患儿进行了血清GM实验,1例阴性;该例患儿入院前曾在外院给予伏立康唑抗曲霉菌治疗,这可能是该患儿GM实验阴性的原因。实验室的质控因素也可能是导致该患儿GM实验阴性的原因。
有文献报道应用阿莫西林和(或)克拉维酸钾、哌拉西林和(或)他唑巴坦等药物的患者可出现交叉反应,血清GM实验可呈假阳性[16]。本研究10例IPA患儿进行了血清GM实验,9例阳性,追查病史,均有使用哌拉西林和(或)他唑巴坦及其他β-内酰胺类抗菌药物史,但均在进行GM实验前至少5d停用,故本研究9例患儿血清GM实验阳性为假阳性的可能性小。
六、治疗
IPA以药物治疗为主,2008年IDSA更新的曲霉菌治疗指南推荐IPA首选伏立康唑[3]。2011年美国胸科学会(Americanthoracicsociety,ATS)发布的新版成人肺部和重症真菌感染治疗指南,也推荐伏立康唑为IPA的初始治疗首选药物[17]。伏立康唑的抗菌机制为通过干扰真菌的细胞色素P450合成,从而干扰真菌细胞膜成分麦角固醇的合成,使细胞膜通透性增加,细胞内重要成分流失而致真菌死亡。本研究13例首选伏立康唑的患儿中7例有效,最终痊愈,治疗有效率54%,与国外报道相近[18]。
总之,对于有IPA高危因素的患儿要高度警惕IPA,需反复多次进行痰涂片及培养、BALF涂片及培养、血培养、血清G实验、GM实验,尽可能进行胸腔积液涂片及培养、肺组织培养及有创的肺活检,争取早期诊断、及时合理治疗。
清热燥湿,杀虫止痒。
健客价: ¥14细菌性阴道炎,滴虫性阴道炎,外阴阴道念珠菌病,阴道炎,妇产科。
健客价: ¥48.9男性身体滋补营养品
健客价: ¥298用于病员做检查、护理、疗养。
健客价: ¥1499口服用于治疗消化道念珠菌病。
健客价: ¥42小型的老人车,旋转式的前轮,移动非常方便。
健客价: ¥998治疗由细菌、滴虫、念珠菌引起的外阴、阴道感染和阴道混合性细菌感染。
健客价: ¥68抗真菌药。适用于治疗白色念珠菌、烟曲霉菌、隐球菌及球孢子菌属等引起的真菌性角膜炎。
健客价: ¥6白色念珠菌和其他念珠菌所引起的阴道炎和外阴感染。
健客价: ¥17伊曲康唑适用于治疗以下疾病:1.妇科:外阴阴道念珠菌病。2.皮肤科/眼科:花斑癣、皮肤真菌病、真菌性角膜炎和口腔念珠菌病。3.由皮肤癣菌和/或酵母菌引起的甲真菌病。4.系统性真菌感染:系统性曲霉病及念珠菌病、隐球菌病(包括隐球菌性脑膜炎)、组织胞浆菌病、孢子丝菌病、巴西副球孢子菌病、芽生菌病和其它各种少见的系统性或热带真菌病。
健客价: ¥40.5伊曲康唑适用于治疗以下疾病: 1.妇科:外阴阴道念珠菌病。? 2.皮肤科/眼科:花斑癣、皮肤真菌病、真菌性角膜炎和口腔念珠菌病。? 3.由皮肤癣菌和/或酵母菌引起的甲真菌病。? 4.系统性真菌感染:系统性曲霉病及念珠菌病、隐球菌病(包括隐球菌性脑膜炎)、组织胞浆菌病、孢子丝菌病、巴西副球孢子菌病、芽生菌病和其它各种少见的系统性或热带真菌病。
健客价: ¥65伊曲康唑适用于治疗以下疾病: 1.妇科: 外阴阴道念珠菌病。 2.皮肤科/眼科: 花斑癣、皮肤真菌病、真菌性角膜炎和口腔念珠菌病。 3.由皮肤癣菌和/或酵母菌引起的甲真菌病。 4.系统性真菌感染 系统性曲霉病及念珠菌病、隐球菌病(包括隐球菌性脑膜炎)、组织胞浆菌病、孢子丝菌病、巴西副球孢子菌病、芽生菌病和其它各种少见的系统性或热带真菌病。
健客价: ¥82本品适用于治疗以下疾病: 1. 妇科:外阴阴道念珠菌病。 2. 皮肤科/眼科:花斑癣、皮肤真菌病、真菌性角膜炎和口腔念珠菌病。 3. 由皮肤癣菌和/或酵母菌引起的甲真菌病。 4. 系统性真菌感染:系统性曲霉病及念珠菌病、隐球菌病(包括隐球菌性脑膜炎)、组织胞浆菌病、孢子丝菌病、巴西副球孢子菌病、芽生菌病和其他各种少见的系统性或热带真菌病。
健客价: ¥18伊曲康唑胶囊适用于治疗以下疾病: 1.妇科:外阴阴道念珠菌病。 2.皮肤科/眼科:花斑癣、皮肤真菌病、真菌性角膜炎和口腔念珠菌病。 3.由皮肤癣菌和/或酵母菌引起的甲真菌病。 4.系统性真菌感染:系统性曲霉病及念珠菌病、隐球菌病(包括隐球菌性脑膜炎)、组织胞浆菌病、孢子丝菌病、巴西副球孢子菌病、芽生菌病和其它各种少见的系统性或热带真菌病。
健客价: ¥15高血压。心绞痛。伴有左心室收缩功能异常的症状稳定的慢性心力衰竭。
健客价: ¥256由皮真菌、酵母菌、念珠菌、曲霉菌引起的皮肤感染,如:体股癣、足癣。
健客价: ¥26- 妇科:外阴阴道念珠菌病。- 皮肤科/眼科: - 花斑癣、皮肤真菌病、真菌性角膜炎和口腔念珠菌病。 - 由皮肤癣菌和/或酵母菌引起的甲真菌病。 - 系统性真菌感染:系统性曲霉病及念珠菌病、隐球菌病(包括隐球菌性脑膜炎)*、组织胞浆菌病、孢子丝菌病、副球孢子菌病、芽生菌病和其它各种少见的系统性或热带真菌病。 *注:对于免疫受损的隐球菌病患者及所有中枢神经系统隐球菌病患者,只有在一线
健客价: ¥1201、妇科:外阴阴道念珠菌病。2、皮肤科/眼科:花斑癣、皮肤真菌病、真菌性角膜炎和口腔念珠菌病。3、由皮肤癣菌和/或酵母菌引起的甲真菌病。4、系统性真菌感染:系统性曲霉病及念珠菌病等。
健客价: ¥391.妇科:外阴阴道念珠菌病。2.皮肤科/眼科:花斑癣、皮肤真菌病、真菌性角膜炎和口腔念珠菌病。3.由皮肤癣菌和/或酵母菌引起的甲真菌病。4.系统性真菌感染:系统性曲霉病及念珠菌病、隐球菌病(包括隐球菌
健客价: ¥261.妇科:外阴阴道念珠菌病。 2.皮肤科/眼科:花斑癣、皮肤真菌病、真菌性角膜炎和口腔念珠菌病。 3.由皮肤癣菌和/或酵母菌引起的甲真菌病。 4.系统性真菌感染:系统性曲霉病及念珠菌病、隐球菌病(包括隐球菌性脑膜炎),组织胞浆菌病、孢子丝菌病、巴西副球孢子菌病、芽生菌病和其它各种少见的系统性或热带真菌病。
健客价: ¥391、妇科:外阴阴道念珠菌病。-2、皮肤科/眼科: - 花斑癣、皮肤真菌病、真菌性角膜炎和口腔念珠菌病。 -3、由皮肤癣菌和/或酵母菌引起的甲真菌病。-4、系统性真菌感染:系统性曲霉病及念珠菌病、隐球菌病(包括隐球菌性脑膜炎)*、组织胞浆菌病、孢子丝菌病、副球孢子菌病、芽生菌病和其它各种少见的系统性或热带真菌病。
健客价: ¥29细菌性阴道病、滴虫性阴道炎、念珠菌性外阴阴道病、阴道混合感染。
健客价: ¥44用于细菌性阴道病、念珠菌性外阴阴道病、滴虫性阴道炎以及细菌、真菌、滴虫混合感染性阴道炎。
健客价: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