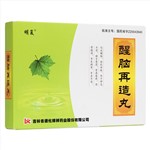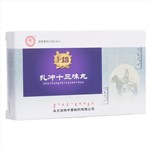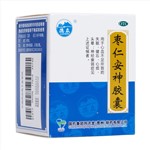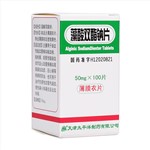油麻菜:记录中医八年,刚开始的时候,我问一位中医,说自己是电视台做纪录片的,想拍摄记录中医。他问我对中医有多少了解?我想了半天想起来,说我妈妈是赤脚医生。
见到那位中医之后,他张口就是太阳病、厥阴病,我彻底听不懂,觉得我一辈子都听不懂,这简直是另一种语言。
潘毅老师不仅是博士生导师,还是专门给国内的一些专家教授们做培训的专家,和他对话,我就很有压力,虽然很熟悉常见面,但是始终没敢面对面正儿八经讨教中医,因为怕他说的我又听不懂。感谢正安广州学院给我们这个机会,让我勇敢的把椅子搬到老师面前。
还没坐下来,一抬头看到我们后面的对联,是可一师写的,我就吓了一跳:“啐啄同时用最难,相逢恰是两疯癫”,我希望跟潘毅老师能够高高兴兴、快快乐乐地做一次很好的交流和谈话,也感谢在座的朋友赶到这边来,听我们两个“疯癫”聊天。
以往正安文化做大型论坛活动的时候,梁冬老师主持,第一个发言或者最后一个发言的人往往请潘毅老师。你就知道他有多强大了。
潘毅:也不见得,也许是我脸皮比较厚。
油麻菜:潘毅老师担任多少年老师了?
潘毅:1982年到现在35年。一直没离开过讲台。
油麻菜:因为离开讲台会饿肚子吗?
潘毅:没有想过,我是去年退休的,退休后我还在正安讲课,全国跑。
油麻菜:前阵子看的《摔跤吧!爸爸》,有些人好像注定一辈子就做这一件事情,只会做一件事情,或者只享受一件事情,我怀疑潘老师也是这种人。就像退休了,绑在家里也绑不住,非要到讲堂上说点什么,因为习惯了。但是我很好奇,老师最早是怎样开始接触学习中医?
潘毅:科班。
油麻菜:小的时候有没有老爷爷摸着你的头,说这个小弟后脑勺长得跟我很像,学中医有出息,天生慧骨......
潘毅:没有,当年读大学的愿望都没,不是没愿望,是没条件。我是文革的高中生,文革期间,高考停招,10年停招,压根没想过大学,后来是做了知青,又做了工人。
油麻菜:还上山下乡过。
潘毅:上山下乡过,1977年恢复高考,其实很突然。我印象中好像是10月份左右宣布高考,12月份就要考,那个时候连教材都无法借全,反正短时间内能拿回多少算多少,结果运气好就考上了。据说当年广东高考的录取率是1%。
油麻菜:那你是有天赋,背功特别好。
潘毅:我是背功特别好,尤其是短期记忆特别好,所以作为学医要通过考试是比较容易的,但我不敢说因为这样基本功就很扎实,确实通过考试对我来说不难。
油麻菜:难怪脑门长得这么亮。当时最开始为什么会选择中医?
潘毅:那个年代和现在不一样。我们那一届的学生高考,不管学什么,只要上线就得去读。我当时是技工学校毕业,要求必须报工科,所以我第一志愿报的是华南理工学院,我第二志愿报的居然是中山大学,不会填志愿,乱填的。第三志愿是填中医学院,因为我妈是搞药的。因为那个年代有一个卫生工作指示,说医务人员要到农村去,我妈就说学中医比较保险,因为公社这一级要不起中医,最差也可以去到县级,是带着这个目的去读中医的。
油麻菜:当时我父母也是上山下乡,父母是赤脚医生,我还是我爸爸接生的......
潘毅:我的不少同班同学是赤脚医生,我们那个年级的年纪最大32岁,年最小16岁,在同一个年级里。
油麻菜:当时对中医的理解,接触到的中医是怎样的?刚开始接触的时候。
潘毅:刚开始进去其实没什么感觉,只是为了读书学习工作走入中医的。客观来说,现在我当大学老师,我从来不批评学生玩手机、看电视等太多,因为我们那个年代没电视,一个年级200多人只有1台14寸黑白电视,节目也不多,所以只能专心读书。
油麻菜:客观上你是没什么事可以做,只好读书。
潘毅:也比较珍惜机会是真的,所以两个要素加在一起,其实我在班上不算用功。
油麻菜:不用功,可是总是名列前茅那个。
潘毅:可以这么说。
油麻菜:当时学中医都是怎么学的?
潘毅:上课老师教,下课就背。我们那个年代的老师还是比较纯,但是教的水平有多高,我也不好说,如果以现在的眼光看,感觉不是太标准,因为那个年代10年没招生。
油麻菜:就连老师回到学校教学生都很新鲜。
潘毅:对,考试也新鲜。
油麻菜:当时刚开始学中医的时候,有没有一见钟情,爱上中医之类,高呼中医万岁真伟大云云?
潘毅:客观来说,我读到毕业好像也没有这种感觉。我大概是不讨厌、基本接受,但谈不上热爱。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临床,中医治病效果能到哪里还未知,而且当时很多医院治疗的病人基本上中医也用、西药也用,你很难判断哪部分是中医起效果,所以实实在在说来是可能有个比较稳定的工作,而且这个职业看上去还蛮受人尊重的,应该还是很原始的一些想法。我不敢说当时就爱哪一行,但不讨厌,还是能做下去。
油麻菜:这是潘老师的性格,平平淡淡、实实在在,反正也没有很惊心动魄、奇怪的事情,比如摔了一跤突然感悟人生,我要发奋学中医,为中华崛起等等。
潘毅:当年我们那个年级就整体而言确有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想法,应该是改造了一代人,但是好像我的反应也不热烈。读大学的时间,读了很多杂书,我觉得这一点对我以后做老师有很大的帮助。
油麻菜:嘿嘿,这一点我们很像,我那时候读了大量的金庸。
潘毅:我应该是大陆最早把金庸全集收集全的呢!当时内地出的第一本是《书剑恩仇录》,我就到香港把港版金庸小说全部买下来,应该是第一批收全的人。
油麻菜:当时《书剑恩仇录》出来的时候,我读小学,哥哥是中学生有学生证,可以到图书馆借书。星期六门一开我们就冲进去,第一个借到书,然后他看一侧我看一侧。不过我觉得这些书里,多少是一个种子种在我们心里,对江湖、对美好、对很遥远地方的一种向往,真的就像一个种子,很美好。
潘毅:而且中国文化的东西在他书里也有不少体验。我们那个年代实际上还有一个好处,文革前出的书相当比例是竖版的,繁体竖版,我们是看惯了繁体竖版的书。所以对于医书、古文不陌生,没有抗拒感,读上去还有亲切感,可能就跟现在的人学中医看古文很陌生有点不同。
油麻菜:等于有一种亲近感,这是从思维模式上先改变了,换成左手拿筷子,然后再开始吃饭。你在读书的时候是很顺的一种状态。
潘毅:我觉得最有益的是,我一辈子喜欢读书,尽管不一定读的都是医书,这个好习惯一直保持下来,真的很受益。
油麻菜:那四年读的书特别多?
潘毅:特别多,因为以前你不可能借到那么多书,但是我可以说,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看小说,一直看到现在都没间断过。
油麻菜:我们刚好相反,我是三年级开始喜欢满山乱跑,从来没有停下来过。潘老师很特别,对书的爱好一直积累到现在,秀才读书,笼中捉鸡,这个话是有道理的。后来除了大学之后,进入到什么阶段?
潘毅:第二个阶段应该是毕业,毕业就是留校做助教,但是做助教我们有一个规矩:当年先到附属医院轮科两年,轮科两年是在病房,每个科大概轮三个月,之后才能回来教学。
油麻菜:就是医院每个科室都要待一待。
潘毅:对,妇科、儿科、急诊等,到第一线轮了两年才回来教学。教学的同时必须要去门诊,所以门诊是一直都在。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特征,就是对工作很负责。其实我以前的性格还是蛮腼腆、内向的。
我留校当时最大的一个害怕就是想着我怎么可能站在台上能够连续讲45分钟课?这是一个很大的害怕,那怎么办?初做老师的时候,先把所有该背的内容,都背得滚瓜烂熟,烂熟之后上了台就有底气,可能一开始上课应该是半背半讲。
但是有两三节下来之后,你感觉到自己背得还是蛮从容的,慢慢就讲得比重越来越多,接着就是将专业名词、术语慢慢地转化为大家听得明白的,开始会说人话。慢慢走上正轨,可能受学生欢迎程度高了,你就越来越自信,越来越坦然,慢慢就越做越好。我个人觉得还是自尊心问题,你站在讲台上,如果下面的学生不搭理你、不听你,眼神没交流或睡觉,那就很没劲了。先不说其他,就为了说得有劲,为了一份自尊,我就得在台上讲好。
油麻菜:当时就在录聚友礼里的时候,潘老师简直是所有老师里面最认真的,每集话题提纲都写下来,录制的时候还一定要站起来的......
潘毅:我做了35年的大学教师,在大学里真没坐下来讲过一节课,一站起来就有气场就有感觉,所以我不能做领导,因为坐下来不会说话。
慢慢成为一个老师,其实中间其实还有一个小插曲,我觉得我不算勤快,很多留校的都选择读研究生,我在熬,慢慢熬了4到5年,出了一个政策说如果不读研究生就不能升讲师,这就很要命了。马上又开始补外语,因为考研究生需要外语,我读研究生三年。
油麻菜:你还会外语啊?
潘毅:中医都得考外语。当时我觉得读研究生时期有一个事情对我触动比较大,或者是我对中医认识的一个转机,大概是1989年,我的研究生课题两年做完了,但是那个时候研究生读三年,没有提前毕业这一说,还有一年就没事做,晃晃悠悠。
刚好那个时候社会上流行气功,结果就玩了一个导引功,玩的时候一是观念的改观。因为原来包括我教中医、我学中医,讲到中医的经络,气的升降出入,尤其讲到气或者升降出入,很容易把它理解为一种中医设定的概念化的东西,方便陈述医理,但是玩了这么一种玩法之后,就明白气是实实在在的,不那么虚。
后来玩了这种入门的东西之后,再玩打坐的过程中,你真的能体会到内气循环的感觉,有了这个垫底之后,对中医的了解就深了很多。
同时我本身也是一个喜欢理论研究的人,一玩到这个我就想形成理论解释,由于研究生的学习背景,当时都有点想将其科学化的观念或痕迹的存在。一玩到理论,我就发现研究气功最早一本专著叫做《周易参同契》,看这本书我看里面有用《易经》来解释的,我又切进了《易经》那个门,再看好像它对气功指导的深广度上可能在医学方面更能呈现,我又回到医学,玩到了《周易》和医学的相关部分,积累到一定时间,就有了之后写的一本书《寻回中医失落的元神》,所以有这么一个因缘存在。因为我刚才讲到一个内气的问题,可能涉及到很多的……
改善睡眠。
健客价: ¥268本试剂用于体外定性的检测妇女尿液中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用于妊娠早期的辅助诊断。
健客价: ¥49养心,益肾,安神。用于神经衰弱症见失眠,多梦,头晕者。
健客价: ¥148化痰醒脑,祛风活络。用于神志不清,语言蹇涩,肾虚痿痹,筋骨酸痛,手足拘挛,半身不遂。
健客价: ¥12补脾胃;益气血;安心神;调营卫;和药性。主脾胃虚弱;气血不足;食少便溏;倦怠乏力;心悸失眠;妇人脏躁;营卫不和。用于脾虚泄泻,心悸,失眠,盗汗,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健客价: ¥15祛风通窍,舒筋活血,镇静安神,除“协日乌素”。用于半身不遂,左瘫右痪,口眼歪邪,四肢麻木,腰腿不利,言语不清,筋骨疼痛,神经麻痹,风湿,关节疼痛。
健客价: ¥27.9主要用于祛风通窍,舒筋活血,镇静安神,除湿。用于半身不遂,口眼斜、四肢麻木、腰腿不利、语言不清、筋骨疼痛、神经麻痹、风湿,关节疼痛等症。
健客价: ¥55祛风通窍,舒筋活血,镇静安神,除“协日乌素”。用于半身不遂,左瘫右痪,口眼歪邪,四肢麻木,腰腿不利,言语不清,筋骨疼痛,神经麻痹,风湿,关节疼痛。
健客价: ¥28.6消肿托毒,排脓,杀虫。用于痈疽初起或脓成不溃;外治疥癣麻风。
健客价: ¥166祛风化痰,活血通络。用于风痰阻络所致的中风,症见半身不遂、口舌歪斜、手足麻木、疼痛拘挛、言语蹇涩。
健客价: ¥119养血安神。用于心血不足所致的失眠、健忘、心烦、头晕;神经衰弱症见上述证候者。
健客价: ¥26.5养血安神。用于心血不足所致的失眠、健忘、心烦、头晕;神经衰弱症见上述证候者。
健客价: ¥30益气补血,健脾养胃。用于白细胞减少症及病后体虚,肝脏亏损所致的免疫力下降等症。
健客价: ¥78用于牙周病引起的牙龈出血、牙周脓肿等病症。
健客价: ¥11.1用于牙周病引起的牙龈出血,牙周脓肿等病症。
健客价: ¥12养肝,宁心,安神,敛汗。
健客价: ¥95通过本品检测尿液,可是女性充分了解自己是否受孕。不需任何容器,直接接尿,方便、卫生、准确、特别适用于家庭自我检测。
健客价: ¥4.8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简称HCG)是妊娠期由胎盘产生的一种糖蛋白激素。 快速早早孕诊断盒经大量试验证实,其准确率达99.8%以上,其灵敏度达10毫国际单位/亳升 (即妇女受孕三天左右)。
健客价: ¥5主要用于缺血性脑血管病如脑血栓、脑栓塞、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及心血管疾病如高血压、高脂蛋白血症、冠心病、心绞痛等疾病的防治。也可用于治疗弥漫性血管内凝血、慢性肾小球肾炎及出血热等。
健客价: ¥7.8补肝益肾,补气养血。用于肝肾不足、气血两虚所致的血虚虚劳,症见心悸气短、头晕目眩、倦怠乏力、腰膝酸软、面色苍白、唇甲色淡、或伴出血;再生障碍性贫血、缺铁性贫血见以上述证候者。
健客价: ¥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