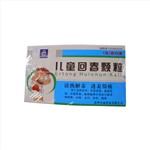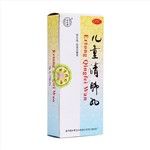管1945年条例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也不是无懈可击的,尤其在下面两个棘手的问题上:儿童与青少年的司法责任以及他们应受到的惩罚。
人们经常大肆批驳这部条例,为各种企图推翻它的做法辩解,理由是它卸除了未成年人的法律责任,使他们逃脱法律制裁。根据那些批评人士的说法(他们通常是“绝对镇压”的支持者),1945年条例完全建立在对青少年理想化甚至天使化的看法,以及家长式司法挂念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普遍不受惩罚的状态。这样的断言显然让人无法认可,但我们能注意到,这些批评并非无的放矢,它们确实反映出了这部条例的一些内在矛盾。
1945年条例的内在矛盾
1945年条例是围绕三个轴线制订的:对儿童时期的认识,与这种认识相应的对儿童的认识,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儿童过错的特别认识。
儿童时期
这部条例是在一种未成年人法律框架内制订的,后者建立在对童年的现代观念上:童年是一段延续的时期,是一个过程。
儿童不再像1810年刑法典描写的那样是一个“微型版成人”,而是一个成长中的人,童年是实现这个成长的时期。
儿童
未成年人的不成熟性,其“发育未完成”的特点及其“儿童状态”所产生的后果都得到了法律的重视,体现于法律赋予儿童的地位:他是一个“尚未”发育完成的人。与成年人不同,儿童“尚未”成为完全的法律主体,“尚未”享有法律主体的所有权利。
在民法上,儿童被认为是“不负法律责任的”(儿童对自己的行为不承担法律责任,而由其父母来承担),是“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儿童不能进行“诉讼”,而应由其父母代理)。
既然没有给予儿童与成人同样的权利,那么从逻辑上讲,法律也不能要求儿童承担与成人同样的义务。所以,刑法减轻了儿童的法律责任,或更准确地讲,刑事责任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逐渐加大。这是根据协调的标准作出的,因为人们的量刑尺度在儿童享有的民事权利及其担负的刑事“责任”之间建立了一致关系(指出这一点很重要)。因此民法规定,从儿童13岁开始,对其收养或更改其姓名必须得到其同意。但也是从这个年龄开始,他就可能受到刑事监禁。
从16岁开始,儿童有权申请法国国籍,也可能受到未成年人重罪法庭的审判(上文已经提到,未成年人法庭做出的判决与成人重罪法庭很接近)或受到临时监禁。
过错
至于儿童所犯过错,上文也曾提到,1945年条例将其视为一种有待解读的病症。因此司法部门不能简单地像对成人那样满足于对其行为定性(如某男是否杀害了某女),而要弄懂当事人的人格:这名未成年人是谁?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可以采取什么措施,在惩罚其行为的同时,让其明白其行为构成轻罪或重罪的原因?
未成年人司法的这种特殊定位在1958年又一次得到明确,当时儿童法官被赋予了另一项职责:“当未成年人的健康、安全或教育条件受到”严重损害“时,要对其进行保护。”1970年,又有一部关于“处于危险中的儿童”的法律出台。
法律赋予儿童“尚未”成人的地位在伦理方面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其目的不是让儿童处于从属地位,不是让儿童服从于某种家长的权威(就像拿破仑法典给予妇女的地位),而是保护脆弱的儿童,赋予其受保护和受教育的权利。
然而,其中仍然存在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它与社会习惯给予儿童的地位出奇的吻合(这一点可能没有得到足够的强调)。不管社会如何描述儿童,它今天仍然借口儿童的不成熟性否定他的“完全主体“地位。的确,一些有关的研讨会或大会结束后(会上充斥着轻浮的华丽辞藻),我们总会听到这样的话:他”年龄还小“,”还不够成熟“,”还不够理智......“总而言之,他”尚未“成人,他的欲望不具有与成人欲望相同的合理性,他所说的话总是无足轻重、”微不足道“。这种现象造成很多后果,因为在现实中,对儿童的习惯看法与儿童的法律地位相结合,因为在现实中,对儿童的习惯看法与儿童的法律地位相结合,共同促使人们心安理得地给予儿童一个缩小的地位,剥夺了他本应享有的基本权利(例如,了解自己的身世和亲生父母的身份,在受到虐待时离家生活等)。
然而,1945年条例赋予儿童的地位造成了第二个后果,那些批评者正确地指出过,该条例将法官和整个社会置于两个近乎陷阱的矛盾之前。
第一个矛盾就是认为儿童不负法律责任,同时却要他接受审判,1945年条例确实为其规定了一个审判机构:未成年人法庭。因此该条例走入了死胡同:如何审判一个已被提前宣布不负法律责任的人?
然而该条例的矛盾并不限于此:它优先考虑教育并由此将惩罚至于第二位(尽管没有完全剥夺了它通常拥有的行为手段:惩罚。
情况很成问题,尤其因为上面提到的困难不在于该条例存在的某些薄弱之处(我们可以指望对其修改),而在于未成人概念本身具有的复杂性,因此也在于人们一旦想重视这个概念就无法回避的一系列问题。
在多米尼克.杨看来,人们的确可以考虑采取两种办法来解决上述矛盾:
1、宣布未成年人不负任何法律责任,停止对未成年人的审判。但这个办法明显行不通;
2、宣布未成年人享有完全的法律主体地位,对其行为负完全的法律责任,审判时也以此为前提。但很明显,这种推翻人们用巨大代价换来的未成年人地位的做法是历史的倒退,是最具危害的倒退,它使人们重新回到司法对成年人和儿童不加区分的时代。
那么如何走出这个死胡同呢?尽管人们付出很多努力,但对这个问题人们似乎从未找到令人满意的回答。这是后果最严重的失败,因为条例的批评者从此可以轻易抛弃这部条例,借口是条例将儿童利益与社会利益对立起来,甚至靠牺牲后者利益来维护前者利益,并由此歪曲司法本身的职能。他们强调说,司法不是为了照顾诉讼者的利益,而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公正。这种论据很可怕,尤其因为公众舆论也随时准备以自己的方式(且随心所欲地)为其鼓噪:”对这些年轻人表示理解是件好事,但这期间他们会砸毁一切!司法要等到什么时候采取严惩其行为呢?“这些话很肤浅,非常容易让人拾用,并导致各种错误行为。
司法判例
理论无法使人走出死胡同,而实践则在以混乱和相当危险的方式去尝试解决。面对犯罪的上升趋势,法庭在佩尔邦法律之前就已经采取了决定。
它们所作的判决越来越趋于给未成年人司法改头换面,使其逐渐失去其特殊性。
人们已经习惯将教育措施留给程度最轻的过错,而对严重的违法行为越来越多地采取刑罚措施。
这因此造成被囚未成年人数量逐年增加的情形,许多法官都指出了这一点。
德尼.萨拉斯和蒂埃里.巴郎热写到:”1998年未成年人司法宣布了13169例针对轻罪的监禁判决,而1993年只有6475例。2001年的监禁判决有7500例。“因此他们总结道:”人们总是说这些青少年完全不受法律制裁,但是对他们的镇压从未如此严厉,涉及犯罪未成年人的诉讼从未发展到如此程度。“
对1945年条例的否定
然而,因为未成年人犯罪现象愈演愈烈,人们终于不再满足于解释法律条文,而是开始宣扬修改法律。这场行动导致了2002年9月9日佩尔邦法的出台。该法通过多种措施推翻了1945年条例所勾画的未成年司法制度。
对于轻度和中度的违法行为(占违法行为中最大一部分),负责审理未成年人案件的不再是”儿童法官“,而是普通法官身份的”社区法官“。从前对13岁以上儿童才能做出的刑事处罚现在对10岁以上儿童就能做出,具体办法是这部法律所称的”教育性惩罚“(禁止进入某个场所,罚没物品等)。如果判决未得到执行,当事儿童则可能被收容。该法还制定一些新名目的罪名,如侮辱教师罪。该法对警方在其他场所拘留10岁至13岁未成年人的条件也放宽了,此前对可被判处7年或7年以上狱刑的轻罪嫌犯的拘留不得超过10个小时,现在改为对可被判处5年或5年以上狱刑的轻罪嫌犯可以拘留12小时。
以前,16岁以下未成年人只有犯了重罪才会受到临时监禁,现在该法规定,13至16岁的青少年如果违反司法控制或从封闭式教育中心逃脱,就可能受到临时监禁的处罚。
最后,”封闭式教育中心“将取代从前的教育性收容机构。未成年人在被判接受司法控制或”接受考验“的情况下将被送往”封闭式教育中心“,在那里接受”教育和教学强化跟踪”。
对1945年条例的这种否定找到了法官、律师及儿童专家们的强烈反对。这点不难明白,因为这种否定标志着一系列的倒退。
佩尔邦法律--未成年人司法的倒退
从这部法律的特殊性来看
1945年以来,未成年人案件的审理者第一次不是特殊身份的法官。他们的许多违法行为改由负责成人案件的法官即社区法官审理。这使得司法历史倒退了一个多世纪,只能造成严重的后果。的确,社区法官被要求接手所占比例最大的中、轻程度违法案件,这些违法行为对续都青少年来说标志着其堕入犯罪、步入歧途的开始。对这种开始,儿童法官一般都有能力加以终止。这一方面是因为儿童法官接受过专业培训,而且经验丰富,能够“破解”未成年人的行为,并通过一定的措施和辅助话语传达给后者一种“有意义的”信息,也就是说,这条信息能够“告诉”、教给未成年人某些东西;另一方面是因为儿童法官与教育和社团界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后者能够向其提供很多有关受审对象的信息,并在现实生活中接受法官的工作。
而社区法官在审理这些中、轻程度的违法案件时,尽管也有权利采取儿童法官采取的措施,但对同样的措施却起不到相同的作用。
因为他们缺乏经验和专业培训,所以这些措施不能具有以前的象征性意义。相反,它们还很有可能被这些与社会和家庭决裂的青少年理解为是一次新的“叱责”,又一句“我警告你,如果你继续......”,如同父母和老师无数次威胁他们的话一样毫无效果;也是一次新的惩罚,和从前一样无效,在他们的眼中毫无意义、不起任何教育作用。
从“教育工作”的角度看
此外,佩尔邦法律在教育工作被赋予的地位方面也产生严重的倒退,因为该法律把儿童当做成人对待,而每位家长都清楚,尽管他们经常演霸王、充硬汉,但从很多方面来讲他们还只是没有长大的孩子。对于任何一个了解10岁儿童的人来说,想到这么小的孩子就要受到刑法处罚(尽管这些惩罚在佩尔邦法中被描述成是处于“教育”的需要),这是十分荒唐的事。的确,在这个年龄,即使有重重护甲,孩子的童年特性也总要呈现出来,还有与之相伴的痛苦与绝望,尤其是对亲情关系、帮助、言语和安全不断产生的强烈需求,任何儿童专家都可以借助这种需求进行工作,尽管它通常通过侮辱和挑衅表现出来。
在我过去工作的医院,我(像其他很多人一样)经常会听到一名这个年龄的孩子(他在自己的小区大搞破坏)在第一个问题之后就在办公室叫喊起来:“你真是个大傻瓜,还有你的心理咨询!”而五分钟后他就会泪流满面(并未自己的眼泪恼羞成怒),这只是因为我对他说了下面的话:“也许你害怕我的‘心理咨询’像你说的那样和平常一样,只是一些空话,对你没有任何用处,并且在这之后,我也会像其他人一样不再管你了。”我就这样趁机钻入他眼泪打开的缺口,补充说:“你不用害怕,我不会放弃你不管的。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一起努力,看看怎样才能让你走出困境。”
把10岁儿童当做成人来对待,这实际上是认可了他的“伪装”、他用来掩盖其脆弱的面具,用精神分析学家唐纳德.温尼科特的话说就是“伪自我”。这使他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即社会整体上与他生活的圈子一样,也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生活可能已经过多地对他施加暴力,这是又一次施暴,并由此使他不得不又一次选择暴力解决问题。
为使惩罚有“教育意义”,单靠宣布它如此是不够的,还需要实施惩罚的人能够弄懂这种惩罚的作用,即对受罚儿童有足够的了解,以正确地衡量惩罚对这名儿童来说所占有的位置,以及可能使之填补的空白。
如果没有这样的领悟力和对自己行动的理解力,那么不管什么样的惩罚,即使当事人谓之有”教育意义“,它对孩子也没有任何意义,就如同从前老师敲打学生手指一样。这些老师的信条是学生听话是戒尺打出来的,就好像胜利是枪杆子打出来的一样,这样小兔崽子们才能彻底地俯首帖耳。
这样的惩罚不会比人们所谓驯狗时对狗的鞭笞更有意义。
从心理工作的角度看
佩尔邦法律在心理工作方面,即人们希望了解未成年罪犯并理解其犯罪动机的意愿所占地位方面,也标志着一种倒退。
尽管该法没有明文否定1945年条例赋予心理调查工作的职能并质疑其重要性,但实际上它已经使上述调查只起到一种形式作用,这在程序和机构设置方面表现得尤其明显。
例如为审理累犯而设的”从快程序“,它从理论上讲是有积极意义的。人们确实可以认为,在很短的时间内(10天至1个月)对违法行为做出判决将有利于当事人觉悟,一劳永逸地使其明白,如果犯罪行为已经是件严重的事,那么重新犯罪更是如此。
然而,事实上“从快程序”几乎不可能产生这样的作用。
惩罚累犯、期望借此真正终止其犯罪行为,这实际意味着人们已经有办法弄明白他“重新堕落”的原因:为什么他会重犯?怎样做才能加以制止?
很显然,法律理应为这些探究确定一个期限,因为如果在违法行为发生很久以后才介入,那么迟迟不到的惩罚可能不会对未成年人产生任何意义。
然而“10天到1个月”的期限明显是不够的。
因此,我们只能对这个期限提出疑问,担心其所表达的就是:人们深信任何调查都是无用的,因为事情的来龙去脉已经很明了......;也害怕这个期限是某种理论的反映(这种理论没有被明确说出来,却很可怕),人们会据此认为一个人偷鸡蛋是因为他生性如此,无论他有多大年龄,因此不再需要追究什么和理解什么,只管严厉打击、以阻止其继续作恶就行了。难道说“小火箭”监狱的幽灵又偷偷地给立法者托梦了吗?
最后,佩尔邦法建立的封闭式教育中心也使人无法再从事对未成年人的心理工作,而过去的管教所却能做到这一点,尽管它们远远不够完善。这些中心的建立带有浓重的镇压意味,致使教育工作者无法在其中找到他们所需的时间、工作视野和支持来,帮助有困难的青少年获得其未能从家庭得到的准则。
一些法官就指出:“这是让高墙来做人该做的工作,完全用牢门和铁窗来体现权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无法相信监禁会有什么教育作用。”
重拾“判断力”标准
佩尔邦法律重新引入了“判断力”的标准,然而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未成年人司法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早已与此标准决裂,它自1912年起就再也没有在法律条文中出现过。的确,既然儿童时期至此已经得到人们的重视,被认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成长和发展过程,那么重新用判断力标准来提出问题(未成年人是否知道他在做什么)就似乎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做法。
但是判断力这个概念并没有完全消失,因为在实际工作中,法律的空白造成问题。的确,1945年条例并没有在刑事范畴上确定成年以及未成年人的年龄界限。
该条例没有说明几岁以上儿童属于“足够大“,可以对自己的违法行为负责,因此也没有说明几岁以下儿童”太小“,还不能受到指控。
为了弥补上述空白,司法判例自1956年起通过最高法院的一份判决(即拉杜布判决)重新引入了判断力的标准。
该判决是针对一名无意伤害他人的儿童作出的,它规定对未成年人的判刑条件必须是当事人”有意且明白“其所实施的行为。最高法院对此判决给出的解释是:”任何违法行为,即使是无图谋的违法行为,其前提必须是肇事者在行动时具有理解力且有意为之“。
这样的论据合情合理,而且评论家也及时指出了这一点:”如果没有这样合理的要求,我们可以想象,假如一名几个月大的婴儿在吃奶时戳瞎了奶妈的一只眼睛,那么他要被送到儿童法庭,受到1945年条例第15条所规定的惩罚。“
判断力的概念一直为司法判例所保留,佩尔邦法律则通过对《刑法典》第122-8条的修改将其重新引入法律条文,自此该法第2条规定:”有判断力的未成年人应对其被认定犯下的重罪、轻罪和治安罪负刑事责任。“
该条第2段则重新使用了因当事人年龄而减轻其刑事责任的概念:”本法同时规定,对10至18岁未成年人可处以教育惩罚,对13至18岁未成年人可以处以刑罚,并根据未成年人的年龄,考虑减轻其刑事责任。“
该法重新引入”判断力“的概念,公开的目的就是要打破根据1945年条例规定的13岁未成年人不能被判刑、”不负法律责任“的思想。
然而,如果我们将其与佩尔邦法规定的所有措施进行横向比较,就会清楚地发现这是历史得倒退。
人们退回到了司法不重视儿童特殊性、不区分儿童与成年人的时代。
像现行刑法典所规定的那样,人们根据判断力来提出未成年人罪责的问题,同时满足于因为后者尚未成人而减轻其责任,这其实等于和从前一样根据数量而非质量去思考问题。
这种思维方式考虑的只是人们根据未成年人年龄来判定他所具有的判断力的”高低“。人们满足于确认孩子年龄越小,其判断力一带你过越低,从而忽视了判断力的本质及其为何与成年人判断力有所不同的问题。这种忽视的潜在意思是:二者之间没有什么不同。不管人们怎么想,这样做其实重新回到了”微型版成人“这个陈腐无比的观念:儿童与成人没有根本性的不同,他只是更小,并因为个子小,脑袋也小......判断力也就低下。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今天,精神病学与精神分析学获得的有关儿童与青少年方面的知识的确已能使人揭示其心理活动和思维活动的复杂性。这些知识使人能够认定,类似下面的话过于简单化:”但是他又不是傻瓜!他很清楚自己在偷那辆自行车!”理由如下:
首先,一名儿童或青少年的“理解力”总是相对的,尤其是对禁忌的理解。一名儿童或青少年的确能够明白(一般情况均如此),他所“借用”的自行车不属于他,他拿走自行车的行为是应受指责的。但是这样的认识对他来说很可能只是自发的,丝毫不“产生意义”。确实,如果他的自身经历没有使他懂得社会规则及其作用,或者更糟糕的是,如果他看到抚养他的成人总是干严重的违法行为而没有受到惩罚,那么“偷”的想法在他看来就无甚危害,这种行为对他来说远非是我们所认为的严重违反规则。在这种情况下,某些未成年人因不满对他们的惩罚,认为惩罚过度或不公,也会清楚地表明这一点:“是的,我真的偷了,但是......”这种想法通常被认为是他们期望受到较轻的惩罚使然,而其实它明显表现出他们并不理解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
其次,对儿童与青少年来说,要让其内心完全接受禁忌,这从来都不是一个既成过程,而永远是一个“进行中”的过程,另外还应强调,这个过程从来都不是线性发展的,而经常交替着前进和后退。
父母和教育工作者对这种情况太熟悉不透了:“真可怕!我们以为这次他已经懂了,但呼啦一下,他又重犯了。”
最后,儿童与青少年从内心接受禁忌的能力,总是取决于他们与使他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成人之间的关系。因此,一名青少年可以瞬时间“明白”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做。但仅过一个月又瞬时间“不明白”了,因为帮助他建立这种认识的人当时不在现场(他还不能独自建立这种认识)。我们在管教所会经常看到这种现象,一旦教育工作者离开管教所,非常依赖他的那名青少年就会故态复萌,这说明他还需要前者的帮助,以透过从自身经历之外获得的眼镜去看这个世界。
成年人是一个已经发育成熟的人,也建立了他的准则和信念。儿童和青少年却是永远处于变化中的正在发育的人。用“判断力”来谈论他们,这是人为地把他们的行为定格在一个特定的瞬间,而这个瞬间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只是他们理解力一个短暂、临时和偶然的状态。
清热润肺,祛痰止咳。用于咳嗽气喘,吐痰黄稠或咳痰不爽,咽干喉痛。
健客价: ¥21清热解毒,透表豁痰。用于急性惊风,伤寒发热,临夜发烧,小便带血,麻疹隐现不出而引起身热咳嗽;赤痢、水泻、食积、腹痛。
健客价: ¥22清热解毒,透表豁痰。用于急性惊风,伤寒发热,临夜发烧,小便带血,麻疹隐现不出引起的身热咳嗽;赤痢、水泻、食积、腹痛。
健客价: ¥32清热解毒,透表豁痰。用于急性惊风,伤寒发热,临夜发烧,小便带血,麻疹隐现不出引起的身热咳嗽;赤痢、水泻、食积、腹痛。
健客价: ¥42帮助乳牙成长过程牙龈所需营养、强健牙龈、坚固牙齿。
健客价: ¥15.8布洛芬混悬液:用于儿童普通感冒或流感引起的发热。也用于缓解儿童轻至中度疼痛,如头痛、关节痛、偏头痛、牙痛、肌肉痛、神经痛。 小儿感冒颗粒:疏风解表,清热解毒。用于小儿风热感冒,症见发热、头胀痛、咳嗽痰黏、咽喉肿痛;流感见上述证候者。 丁桂儿脐贴:健脾温中,散寒止泻。适用于小儿泄泻,腹痛的辅助治疗。 兵兵退热贴:小儿感冒引起的发烧、头痛、鼻塞、烦躁、哭闹等。其他原因引起的发烧辅助治疗及应急
健客价: ¥135止痕止痒,对痕痒、昆虫咬伤、皮炎、丘疹、湿疹、汗疹有一定功效。
健客价: ¥59.8清肺,解表,化痰,止嗽。用于小儿风寒外束、肺经痰热所致的面赤身热、咳嗽气促、痰多黏稠、咽痛声哑。
健客价: ¥24用于儿童普通感冒或流感引起的发热。也用于缓解儿童轻至中度疼痛,如头痛、关节痛、偏头痛、牙痛、肌肉痛、神经痛。
健客价: ¥188清热解毒。用于外感风热引起的感冒,症见发热、头痛、鼻塞、喷嚏、咽痛、全身乏力、酸痛。
健客价: ¥21.5清热解毒,透表豁痰。用于急性惊风,伤寒发热,临夜发烧,小便带血,麻疹隐现不出引起的身热咳嗽;赤痢,水泻,食积,腹痛。
健客价: ¥25补充儿童少年体内维生素等。
健客价: ¥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