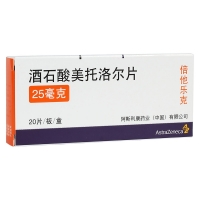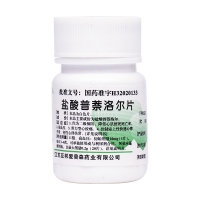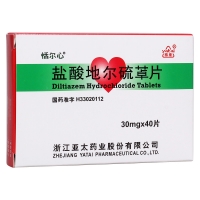肥厚型心肌病(hypertrophiccardiomyopathy,HCM)是影响儿童和青少年第二常见的心肌疾病,也是年轻运动员猝死的主要原因[1-2]。儿童HCM的发病率尚不明确,来自芬兰、澳大利亚和美国的流行病学资料估计,儿童HCM的年发病率为0.24‰~0.47‰[1-3]。2016年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心血管学组儿童心肌病精准诊治协作组回顾性调查了国内16家医院2006—2016年10年间的1823例心肌病住院患儿,其中HCM占9.4%(不包括门诊诊断的HCM)。由于儿童HCM的病因学、遗传学、血流动力学、电生理和临床特征具有高度异质性,这使得人们对儿童HCM的认知不完整,因此,儿童HCM的精确评估和诊断治疗具有巨大的挑战性。同时,由于有关儿童HCM诊治的前瞻、随机、双盲、对照临床研究极其少见,造成有关儿童HCM诊治的措施均以借鉴成人HCM的专家共识为主。2017年国内发布了《中国成人肥厚型心肌病诊断与治疗指南》[4],但迄今为止尚未有儿童HCM的诊断和治疗建议、共识或指南。随着人们对儿童HCM重视程度的提高和儿童HCM分子遗传学研究的快速进展,儿童HCM的诊治迎来了难得的机遇,但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此,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心血管学组儿童心肌病精准诊治协作组与《中国实用儿科杂志》编辑委员会制定了国内首部《中国儿童肥厚型心肌病诊断的专家共识》。
1.儿童HCM精准诊断的机遇与挑战
1.1儿童HCM的形态学诊断1958年Teare[5]首次对肥厚型心肌病进行了详细介绍;2003年美国心脏病学会(ACC)和欧洲心脏病学会(ESC)首次发布HCM专家共识[6];2011年美国心脏病学院基金会(ACCF)/美国心脏协会(AHA)发表了第1部HCM诊断与治疗指南[7];2014年ESC也发布了新的HCM诊断与治疗指南[8]。ACCF/AHA和ESC指南均包括了儿童HCM的诊断标准,均将左心室壁厚度增加超过同年龄、同性别和同体表面积儿童左心室壁厚度平均值加2个标准差(Z值>2)作为HCM的形态学诊断标准;该标准重点强调了包括心脏超声、磁共振成像、CT等影像学诊断手段在HCM诊断中的重要价值[7-8]。但目前缺乏有关该标准在儿童HCM中诊断价值的研究,其诊断的敏感性、特异性和准确性如何尚无明确的结论。由于种族不同,儿童左心室壁厚度必然存在差异,因此该诊断标准是否适合国内儿童,亦不得而知。
由于不同年龄小儿超声心动图的测定值变化较大,相同年龄小儿受遗传、种族、性别、身高、体重、生长速度、生活习惯和疾病等影响也存在差异;这些因素大大影响了测定结果的判断和比较。虽然,国外制定了小儿超声心动图定量分析指南,建议测定结果采用经年龄、身高、体表面积等标准化转换的Z值表达[9-10];但国内小儿超声心动图测量指标Z值的计算多采用国外公式,尚缺乏小儿超声心动图定量分析指南或共识,缺乏适合国情的、权威的小儿超声心动图测量指标Z值计算方法,此为国内儿童HCM的超声学诊断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建立基于国内儿童心脏超声测量指标Z值标准的儿童HCM诊断标准并评价其诊断价值成为今后儿科心血管医师和超声诊断医师的新的研究方向。同时,由于儿童HCM心室肥厚的部位、梗阻出现的时间和程度、整体收缩和舒张功能状态等与患儿的年龄、病因等密切相关,此与成人HCM有很大不同,因此如何建立基于国内儿童HCM超声诊断数据的儿童HCM超声评估标准亦为儿科超声诊断医师的新挑战之一。
2015年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牵头制定了《心肌病磁共振成像临床应用中国专家共识》,提出若条件允许,所有确诊或疑似HCM的儿童患者均应行心脏磁共振成像检查[11]。但儿童与成人相比,体积小,呼吸频率及心率快,呼吸不平稳,且多不配合,需要镇静或麻醉后检查,获得的图像有一定伪影或图像质量不如成人,影响了心脏磁共振成像在儿童HMC中的应用。国内尚未制定包括HCM在内的儿童心肌病磁共振成像检查及诊断的相关共识或指南,此为广大儿科心血管医师和影像科医师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投入更多的研究精力,尽早开展多中心、大样本、规范的儿童心肌病患者心脏磁共振成像研究,尽快制定国内儿童心肌病磁共振成像检查及诊断的共识或指南以提供中国自己的临床证据,成为今后儿科心血管医师和影像诊断医师另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1.2儿童HCM的病因学诊断儿童HCM病因复杂,具有高度异质性,明确儿童HCM病因难度很大[12]。除肌小节基因突变造成的HCM外,尚包括先天性代谢障碍、神经肌肉疾病和畸形综合征;其中代谢型或畸形综合征型HCM多在婴儿期或幼儿期出现症状,而神经肌肉疾病型HCM多在青春期出现;虽然目前此3种病因在儿童HCM病因中的比例均不超过10%[12],但随着分子遗传技术的进步和人们对该类疾病认识程度的提高,相信此3种病因在儿童HCM病因中的比例将进一步提高。因此,儿童HCM的病因诊断需心血管、代谢、神经、遗传等多学科专家共同参与;即便如此,目前1岁以下婴儿HCM中仍有超过50%患者无法明确病因,此为儿科心血管医师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基于上述事实,本期《中国实用儿科杂志》刊登的《中国儿童肥厚型心肌病诊断的专家共识》中首次提出了国内儿童HCM的病因诊断流程;但其应用价值尚需要通过儿科心血管医师的广泛临床应用而得以进一步验证和提高。对于入院短期内即发生死亡、或因病情危重而快速死亡或猝死,或高度怀疑先天性代谢异常(inbornerrorsofmetabolism,IEM)的HCM患儿,应在征得患儿法定监护人同意后留取血标本和(或)尿标本以及组织标本,积极开展代谢性尸检(postmortemmetabolicscreening)和基因性尸检(postmortemgenetictesting)[13]。
2013年国内制定了包括HCM在内的儿童心肌病遗传代谢性病因的诊断建议[14];但IEM种类繁多,迄今为止发现的IEM已超过1000种,而目前被认识的新生儿期起病者仅约100多种,因此IEM的诊断和筛查技术需要进一步提高。同时,同一种IEM可引起不同的心肌病类型,而同一种心肌病亦可由不同的IEM引起,如HCM可由糖代谢障碍或脂肪酸代谢障碍等引起,而脂肪酸代谢障碍可造成扩张型心肌病或HCM[14-15],此为儿童HCM的精准诊断带来困惑。联合应用液相色谱-串联质谱(LC-MS/MS)和气相色谱-质谱(GC-MS)是诊断IEM的主要手段[14-15],但其局限性也应引起儿科临床医师的高度重视。
儿童HCM基因检测的总阳性率可达80%[16],因此推荐所有HCM患儿行基因筛查。基因诊断对于基因性/家族性HCM有明确的诊断价值,但由于20%~30%的HCM先证者无家族史,而有HCM家族史的先证者中有50%~60%(成人和儿童)为编码肌小节蛋白的基因变异;约6%的受累者具有一个以上的肌小节蛋白基因变异(包括一个基因的双等位变异或多个基因的杂合变异),低于6%的受累者具有一种类型以上的致病性变异[17-18],因此如何进一步提高无家族史HCM患儿基因诊断的阳性率,如何确定儿童HCM的复合杂合致病性变异及其价值,成为儿童HCM基因诊断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同时,基因性HCM具有遗传异质性,包括环境、基因修饰、免疫等在内的多种因素会影响其预后,不单独取决于某个特定基因或特定突变;即使在同一家系中携带同一突变的个体也可出现不同的临床表型和预后,因此家系研究是HCM致病基因研究的另一个新的挑战和机遇[13]。儿童HCM尚有众多非肌小节基因突变疾病[4,11-12,17-18](表1),更大大增加了儿童HCM基因诊断的复杂性和难度。本期《中国实用儿科杂志》刊登的《中国儿童肥厚型心肌病诊断的专家共识》中也提出了儿童HCM基因检测解读和临床处理的流程,但该流程尚需要进一步的临床验证和改善。
目前,基因商业化检测作为新兴行业广泛开展,吸引了大量的人才和资金,但参与方的专业技术能力和诚信水平参差不齐,测序信息和临床信息有效分析和解读能力和水平更是高低不一,临床专业医师参与测序数据解读的意识严重缺失;同时,由于儿童HCM病因的高度异质性和复杂性,导致目前基因商业化检测在包括HCM在内的儿童心肌病中的应用和意义受到质疑,成为包括HCM在内的儿童心肌病精准诊断的重大挑战之一。借助大数据技术,通过国内多中心临床数据、随访数据与遗传检测数据的结合,建立检测机构、数据解读人员、临床医师和遗传基础研究人员等多方密切合作的多学科合作团队,深度分析包括HCM在内的儿童心肌病的发病因素、遗传背景、临床表型、诊断、用药、疾病演变及预后之间的关系,成为当前包括HCM在内的儿童心肌病基因精准诊断的重要新机遇之一。
2.儿童HCM精准治疗的机遇与挑战
2.1儿童HCM的病因治疗儿童肌小节基因突变型HCM的基因治疗总体尚处于动物实验阶段,但毋容置疑的是这将是今后儿童HCM治疗的重大机遇和挑战。2017年肌凝蛋白抑制剂mavacamten(Myk461)在PIONEER-HCM二期临床试验中显示能显著改善HCM患者的舒张功能[19];动物实验显示腺病毒相关MYBPC3可抑制突变mRNA的表达,阻止HCM的发生[20];人体随机初步试验显示,在未出现左室心肌肥厚前,给予肌小节基因突变者地尔硫卓可延迟心肌肥厚进展,同时MYBPC3基因突变携带者对地尔硫卓反应较MYH7基因突变携带者好[21]。儿童非肌小节基因突变型HCM的病因治疗的关键是明确病因(表1)[4,11-12,17-18,22-24]。如酶替代疗法对庞贝氏病和法布里病的治疗具有里程碑的意义[22-24],但仍存在终生用药、费用极其昂贵等诸多问题。尽管随着生化检测技术和遗传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很多儿童非肌小节基因突变型HCM的病因得以明确,但遗憾的是目前仅有少数非肌小节基因突变型HCM能够给予病因治疗,这是儿童HCM治疗面临的另一个重大挑战。
2.2症状型HCM的治疗由于婴儿期HCM出现心衰与高病死率密切相关[25],因此婴儿期HCM伴心衰的治疗是儿科心血管医师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棘手问题。利尿剂可以应用,但对于严重左室流出道梗阻的患儿还应慎用;虽有研究发现β受体阻滞剂、维拉帕米和二吡胺可改善婴儿左室流出道梗阻症状[26-27],但所有这些治疗措施均未经多中心前瞻性的临床研究证实;因此,开展婴儿期HCM伴心衰治疗优选方案的大样本、多中心、前瞻性的临床对照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室性心律失常,尤其是持续性或非持续性室速是儿童HCM的高危因素之一[25,27],因此HCM伴心律失常的治疗是儿科心血管医师面对的另一个棘手问题。对于非持续性或持续性室速的临床处理首选胺碘酮和(或)β受体阻滞剂,预防首选安装植入式心律转复除颤器(ICD)[28],但这些治疗措施在儿童的适应证和应用时机等也未经多中心前瞻性的临床对照研究所证实。国内外指南均制定了成人HCM伴房颤的处理原则和方法[4,6-8],但儿童HCM的房颤处理尚无指南供参考,尤其是抗凝剂应用的指征、时机、剂量、疗程及远期预后均无基于儿童的临床研究数据;目前,儿童HCM并房颤节律的控制可参考成人指南给予索他洛尔和胺碘酮,心率的控制可选用β受体阻滞剂和非二氢吡啶类钙通道阻滞剂。
2.3儿童HCM左室流出道梗阻的治疗儿童HCM伴有症状的左室流出道梗阻须根据其严重程度及风险评估情况及时给予包括药物治疗、手术治疗、起搏治疗和消融治疗在内的综合处理,但应合理把握适应证且规范治疗[13]。β受体阻滞剂是治疗儿童HCM有症状的左室流出道梗阻的首选药物,常用心得安、美托洛尔、比索洛尔或阿替洛尔;效果不佳时可加用二吡胺6~20mg/(kg·d),维拉帕米3~7mg/(kg·d)亦可应用[12,25-28];遗憾的是目前尚缺乏上述药物选用指征、干预最佳时机、最佳剂量及合适疗程的循证研究。对于药物治疗无效的难治性梗阻症状患儿,间隔切除术是可供选择的治疗方案之一[29-31],但其远期预后尚未被公认的大样本、前瞻性临床数据所证实。关于儿童HCM的起搏治疗,应严把适应证,目前的证据支持仅限于因严重并发症而不能行手术治疗或有安装ICD指征者[12,32]。儿童HCM的心肌消融治疗(射频消融、酒精消融等)目前尚处于试验研究阶段[12,33],尚无充分证据支持用于儿童HCM。儿童HCM心脏移植的总体存活率较高,但供体心脏的缺乏和长期免疫抑制剂的应用是其致命缺点[12,25-28]。
儿童HCM伴无症状型左室流出道梗阻的处理仍存在较大争议,药物治疗对无症状HCM伴左室流出道梗阻患儿的长期效果尚不清楚;最近一项青少年和成人的回顾性数据表明,心得安或维拉帕米可提高无症状HCM伴左室流出道梗阻患儿的存活率[12,25-28]。目前建议儿童无症状HCM伴左室流出道梗阻的治疗指征为梗阻压差>75mmHg(1mmHg=0.133kPa)[12,25-28]。
2.4儿童无梗阻型HCM的治疗目前此类患儿的治疗经验相对丰富,β受体阻滞剂、钙通道拮抗剂(维拉帕米和地尔硫卓)可改善左室充盈,减少心肌缺血;若存在因左室收缩功能障碍引起的心衰可采用常规抗心衰药物治疗。儿童无梗阻型HCM伴有的心肌桥是否引起心肌缺血以及是否影响预后存在争议[34],但目前尚无充分证据支持心肌桥与心源性猝死(suddencardiacdeath,SCD)相关。总之,对儿童无梗阻型HCM,药物治疗可能不是必需的,但需临床定期评估[13]。
3.儿童HCM危险分层的机遇和挑战
婴儿期后确诊的HCM中猝死是最常见的死亡原因,早期HCM患儿的队列研究显示年猝死率为3%~8%[35],但随后的流行病学研究发现婴儿期后HCM儿童SCD的总体发生率较低,每年为1%~2%[36];新近一项对150例HCM患儿的研究中发现9~14岁儿童SCD(7.2%)明显高于16岁以上儿童(1.7%)[25],提示不同年龄组HCM患儿的死亡风险不同,但目前国内外尚无基于年龄分层的儿童HCM患儿死亡风险评估系统或指标。
成人HCM指南早已提出了基于SCD危险分层的成人HCM危险分层方法,其指标包括SCD家族史、严重左室肥厚、不明原因晕厥、非持续性室速以及直立低血压或运功后低血压,并推出了新的SCD个体化风险评估工具(HCMRisk-SCD方程),这些危险分层方法和个体化风险评估工具在成人HCM的规范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4,6-8]。但成人HCM的风险预测指标和个体化风险评估工具是否适用于儿童HCM尚不得而知。不明原因晕厥、SCD家族史、严重左室肥厚,运动相关血压异常虽与HCM患儿SCD的发生相关,但不是预测儿童和青少年HCM发生SCD的敏感指标,大多数死于HCM的儿童和青少年患者缺乏死前存在非持续性室速的证据[37-38]。2012年Moak等[12]提出了有别于成人的儿童HCM心源性猝死危险因素建议,包括非持续性室速、晕厥、严重左室肥厚、QT离散度、心肌桥、左室肥厚心电图的电压标准、心率变异性、诊断时年龄、电生理可诱导的室速以及血流动力学受限等,但这些危险因素的个体化预测价值及计算方法尚需进一步验证和开发。因此,目前国内外尚缺乏针对儿童HCM的系统风险分层方法,建立基于儿童HCM大样本、多中心、前瞻性数据支持的儿童HCM的风险分层方法和个体化评估工具是儿科心血管医师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
2014年ESC指南建议对曾发生心脏骤停或持续性室速的儿童HCM植入ICD(IB);对于有不少于两个主要儿科危险因素的儿童,经系统评估后发现ICD植入有益者可考虑植入ICD(ⅡaC);对于只有一个主要儿科危险因素者,经严格的系统评估后发现ICD植入有益,在充分告知后可考虑植入ICD(ⅡbC)[8]。但也应注意到儿童ICD植入的并发症远高于成人,因此HCM儿童ICD植入的适应证仍应进一步根据积累的基于儿童年龄和个体危险因素等在内的系统证据来不断完善。药物治疗不能改变儿童HCM的自然病程和预防SCD,其部分原因可能与药物种类或剂量有关[39-41];儿童和成人的研究表明大剂量心得安(每天>6mg/kg)可提高HCM患者的存活率,但缺乏随机对照研究证据支持,且目前大剂量β受体阻断剂的使用还未被普遍接受[39-41]。对于儿童HCM,应建议避免竞技性或剧烈运动,因为SCD最可能发生在体力活动期间;但必须充分认识到无证据支持定期、适度的有氧运动增加SCD风险[41-42]。
4.儿童HCM家系成员的管理和遗传咨询的机遇和挑战
对有遗传风险的儿童HCM患者的直系亲属和其家庭成员进行评估是儿童HCM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儿童一旦确诊HCM,其兄弟姐妹、父母和其他亲属均应进行临床评估,此有助于使无遗传风险的亲属放心。对于可能有危险的家系成员,可用心电图和超声心动图来筛查和评估。成人HCM指南建议家系成员的临床筛查从10~12岁开始,每隔1~2年进行1次,20岁后频率可降低到每2~5年1次[4,6-8]。但最近儿童HCM的基因研究结果表明,对10岁以下儿童开始临床筛查是恰当的[18]。目前国内外尚无儿童HCM患者家系成员的筛查指南或准则。2012年,Moak等[12]提出儿童HCM患者家系成员的筛查应从婴儿期开始,其筛查频率为婴儿期1次,>2~8岁者每2~3年1次,>8~12岁者每年1次,>12~20岁者每6~12个月1次;但该筛查建议的实用性和临床价值尚需进一步验证。
随着分子遗传学检测作为一种有用的诊断工具进入临床领域,临床确诊的HCM患者可行基因检测;若发现致病突变,可对亲属进行基因检测,但应在经认证的诊断实验室进行。2014年ESC新版指南制定了详细的家系成员遗传咨询和检测规则,建议HCM患者的家系成员应行遗传咨询,对于病因无法完全以非遗传因素解释的HCM患者,无论后续是否计划对患者进行临床或遗传检查筛选,均建议对患者家族成员行遗传咨询(IB)[8]。遗传咨询和遗传检测应在专门从事遗传性心肌病的中心进行,应由训练有素的多学科医师实施,应充分考虑患者的自愿性、保密性和心理社会伤害(包括丧失自尊和幸存者负罪感)等问题,尤其需仔细考虑在幼儿中行预测性基因检测是否适当的问题[8,12]。但国内目前尚无儿童心肌病的遗传咨询指南可供参考,对其实施规范性的认识亦严重缺失,因此儿童HCM规范性的遗传咨询尚有较长的路要走。
总之,儿童HCM具有高度异质性,以明确病因为目标的精准诊断面临着诸多困惑和挑战,个体化的风险评估和治疗以及规范的家系管理和遗传咨询尚需制定或完善基于儿童HCM证据的共识或指南。
用于治疗高血压、心绞痛、心肌梗死、肥厚型心肌病、主动脉夹层、心律失常、甲状腺功能亢进、心脏神经官能症等。近年来尚用于心力衰竭的治疗,此时应在有经验的医师指导下使用。
健客价: ¥6.5用于治疗高血压、心绞痛、心肌梗死、肥厚型心肌病、主动脉夹层、心律失常、甲状腺机能亢进、心脏神经官能症等。近年来尚用于心力衰竭的治疗,此时应在有经验的医师指导下使用。
健客价: ¥131.作为二级预防,降低心肌梗死死亡率。 2.高血压。 3.劳力型心绞痛。 4.控制室上性快速心律失常、室性心律失常,特别是与儿茶酚胺有关或洋地黄引起心律失常。可用于洋地黄疗效不佳的房扑、房颤心室率5.的控制,也可用于顽固性期前收缩,改善患者的症状。 6.减低肥厚型心肌病流出道压差,减轻心绞痛、心悸与昏厥等症状。 7.配合α受体阻滞剂用于嗜铬细胞瘤病人控制心动过速。 8.用于控制甲状
健客价: ¥19.81.冠状动脉痉挛引起的心绞痛和劳力型心绞痛。2.高血压。3.肥厚型心肌病。
健客价: ¥11.9用于治疗高血压、心绞痛、心肌梗死、肥厚型心肌病、主动脉夹层、心律失常、甲状腺机能亢进、心脏神经官能症等。近年来尚用于心力衰竭的治疗,此时应在有经验的医师指导下使用。
健客价: ¥8.51.冠状动脉痉挛引起的心绞痛和劳力型心绞痛。2.高血压。3.肥厚型心肌病。
健客价: ¥17用于治疗高血压,心绞痛,心肌梗死,肥厚性心肌病,主动脉夹层,心律失常,甲状腺动能亢进,心脏神经官能症
健客价: ¥4.8用于治疗高血压、心绞痛、心肌梗死、肥厚型心肌病、主动脉夹层、心律失常、甲状腺机能亢进、心脏神经官能症等。近年来尚用于心力衰竭的治疗,此时应在有经验的医师指导下使用。
健客价: ¥6.2用于治疗高血压、心绞痛、心肌梗死、肥厚型心肌病、主动脉夹层、心律失常、甲状腺机能亢进、心脏神经官能症等。近年来尚用于心力衰竭的治疗,此时应在有经验的医师指导下使用。
健客价: ¥5用于治疗高血压、心绞痛、心肌梗死、肥厚型心肌病、主动脉夹层、心律失常、甲状腺功能亢进、心脏神经官能症等。近年来尚用于心力衰竭的治疗,此时应在有经验的医师指导下使用。
健客价: ¥12.5用于治疗高血压、心绞痛、心肌梗死、肥厚型心肌病、主动脉夹层、心律失常、甲状腺机能亢进、心脏神经官能症等。近年来尚用于心力衰竭的治疗,此时应在有经验的医师指导下使用。
健客价: ¥17用于治疗高血压、心绞痛、心肌梗死、肥厚型心肌病、主动脉夹层、心律失常、甲状腺机能亢进、心脏神经官能症等。近年来尚用于心力衰竭的治疗,此时应在有经验的医师指导下使用。
健客价: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