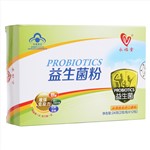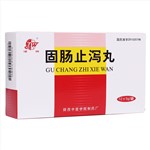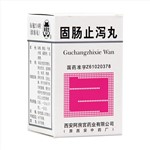专题笔谈│益生菌在儿童抗生素相关性腹泻病的应用!
儿童是滥用抗生素的重灾区和最大受害者,抗生素相关性腹泻(antibiotic-associateddiarrhea,AAD)是指抗生素扰乱和破坏肠道菌群稳态,是临床上最为常见的副反应。AAD的定义:在抗生素治疗2h至2个月的过程中发生无法解释的腹泻,这种腹泻时间超过2d,每天2次以上不成形稀便或水样便[1]。艰难梭菌(clostridiumdifficile,CD)感染是AAD中的严重结肠炎类型。益生菌在抗生素使用期间或之后可能是通过恢复肠道微生态平衡,修复肠黏膜上皮细胞以及恢复肠黏膜免疫和全身免疫活性的方式发挥作用,并且有关益生菌用于防治AAD证据的研究报道逐渐增加[2]。
1AAD
AAD的发生率为5%~39%,门诊儿童AAD的发生率为6.2%,儿科肺炎使用抗生素后腹泻的发生率为50%[3]。门诊和住院儿童AAD中CD相关性腹泻(clostridiumdifficile-associateddiarrhea,CDAD)发生率为6.6%~11.7%[1]。儿童AAD发生的风险存在很大差异,主要的风险因素是宿主因素(年龄和饮食结构)、抗菌药物因素(药物的类型、剂量和疗程)、住院以及并发症。<2岁婴儿、人工喂养、剖宫产、早产以及添加辅食等,AAD发生率风险增加。几乎所有抗菌药物均可以引起儿童AAD,但以林可霉素、头孢菌素类、阿奇霉素、青霉素类(包括氨苄西林、阿莫西林等)为常见,尤其是第三代头孢菌素类抗菌药物[4-5]。绝大多数AAD的病原菌尚未明了。CD是已被肯定的AAD病原体,25%~33%的AAD由CD引起。其他的病原体如金黄色葡萄球菌、产肠毒素产气荚膜梭菌、产酸克雷伯菌和念珠菌属等病原体可能也会导致AAD[1]。
1.1AAD的发病机制AAD的发病机制复杂,目前尚未完全清楚。正常人体肠道生理菌群中90%以上是厌氧菌,少量是兼性厌氧菌和需氧菌,也有极少量过路菌(如肺炎克雷伯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变形杆菌等),肠道正常菌群在机体发挥着重要的生理功能,包括:生物、化学、免疫屏障作用;促进机体代谢和营养作用;生物拮抗作用;免疫赋活作用;维持内环境稳定作用等。抗生素使用后,短期和长期的影响是肠道菌群的结构改变,多样性减少,菌群组成结构重新分布。肠道菌群结构的改变导致肠道可用资源和细菌种群之间相互作用的改变,开放病原菌侵入结合位点以及导致定植抗力的丧失[6]。抗生素引起肠道菌群的多样性减少,延缓有益菌群如双歧杆菌或乳酸杆菌的定植,诱导耐抗生素机会菌株的定植,导致以下改变[7-8]:(1)肠道菌群失衡紊乱,肠屏障保护性菌群被消灭,条件致病菌数量异常增多,肠道黏膜屏障损伤,消化吸收代谢受到影响,从而导致AAD发生,尤其是<2岁的儿童,肠道菌群处在发育和构建阶段,是AAD高发人群。(2)宿主肠黏膜免疫应答模式变化,感染易感性增高,肠腔内微生物相关分子模式(MAMPs)发生改变,这种变化被宿主肠上皮细胞(IEC)表面的模式识别受体(PRRs)所感知,这种IEC与肠道优势菌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发生变化,导致肠壁杯状细胞分泌的细胞间紧密连接蛋白量降低,增加了肠壁通透性,发生细菌移位和肠源性感染。(3)干扰糖和胆汁酸代谢:肠道生理性细菌明显减少,使多糖发酵成短链脂肪酸(SCFA)减少,未经发酵的多糖不易被吸收,滞留于肠道而引起渗透性腹泻。抗菌药物应用后,具有去羟基作用的细菌数量减少,特别是具有7α-去羟基功能的细菌数量很低时,鹅脱氧胆酸的浓度增加,强烈刺激大肠分泌,常继发分泌性腹泻[1]。
1.2CDAD的发病机制CDAD是AAD中的严重结肠炎类型。大多数CDAD病例是医院内获得性感染,但社区获得性CD感染也在逐年增加。研究表明,1个月健康婴儿的CD定植率为70%,2岁健康儿童的定植率为33%,人工喂养儿的定植率高于母乳喂养儿,这种高定植率、无症状可能与新生儿未成熟肠道缺乏肠道正常菌群的保护和肠上皮毒素A受体位点不成熟或数量少有关[9]。CDAD的发病机制主要与抗生素破坏肠道微生物菌群结构、减少碳水化合物酵解、损害胆汁酸代谢、选择出耐药的CD菌株异常生长繁殖、利于病原菌繁殖的结合位点暴露以及肠道黏膜免疫应答紊乱等机制有关,毒素A、毒素B和二元毒素在CD感染发病中有至关重要的作用[10-11]。
2益生菌预防和治疗AAD
由于抗生素改变肠道菌群的结构,菌群多样性减少和菌群组成结构重新分布,导致肠道可用资源和细菌种群之间相互作用的改变,健康的肠道菌群稳态被破坏[6]。恢复或重建健康肠道菌群的措施有补充益生菌、特异性改变肠道菌群组成和(或)活性的益生原和粪菌移植。策略是停止使用广谱抗生素或使用窄谱抗生素;在肠道菌群紊乱后,致病菌繁殖前及时进行干预[11]。
2.1益生菌的作用机制益生菌生物功能的机制包括[12]:(1)减低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产生和增加黏蛋白2(MUC2)表达,减少肠上皮凋亡和增加黏蛋白产生,增强肠屏障功能;(2)增加丁酸产生或上调防御素和抗菌肽水平,增加宿主抗微生物多肽产生;(3)产生小分子有机酸,减低肠腔pH值,以及产生细菌素或小菌素发挥抗菌作用;(4)直接或间接产生阻止致病菌黏附的蛋白,与致病菌竞争上皮结合黏附位点,发挥竞争拮抗作用;(5)减少白介素-8(IL-8)分泌或阻断反调节因子IκB降解,阻断促炎症分子,增加IgA产生,增强黏膜免疫等调节免疫模式;(6)阻断致病菌群体感应信号,干扰致病菌群体之间的联系。由此,益生菌作为功能性营养素,类似于药品(国内已作为药品)广泛应用于儿科临床,用于治疗急性感染性腹泻、肠易激综合征、AAD、炎症性肠病、过敏性疾病等[13-14]。
2.2益生菌预防和治疗AAD现状AAD是个日益严重的问题,而益生菌应用于预防AAD的治疗日趋广泛。国内一项Meta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鼠李糖乳杆菌(LGG)、布拉格酵母菌和双歧杆菌+乳杆菌+嗜热链球菌复合制剂预防AAD的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RR值分别为0.38、0.19和0.24。嗜酸乳杆菌+婴儿双歧杆菌、乳酸双歧杆菌+嗜热链球菌和长双歧杆菌+LGG(KL53A)+植物乳杆菌(PL02)等复合制剂预防AAD的发生率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RR值分别为0.47、0.52和0.47。汇总分析结果显示,益生菌预防AAD的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RR=0.36[15]。2015年Cochrane发布益生菌预防儿童AAD研究报告,共纳入23项随机对照试验(RCT),入选儿童有3938例,年龄2周至18岁,试验所用益生菌为乳杆菌属、双歧杆菌属、芽孢杆菌属、丁酸梭菌、链球菌属、乳球菌属或布拉格酵母菌等,单菌或复合制剂,剂量在5×106~1×1010菌落形成单位(CFU)/d。抗生素与益生菌同时应用,益生菌使用时间范围1~12周。分析结果显示,益生菌组AAD发生率为8%,安慰剂组为19%(RR0.46,95%CI0.35~0.61;异质性I2=5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GRADE分析为中等质量)。所有益生菌制剂中,仅有LGG或布拉格酵母菌剂量在(5×109~4×1010)CFU/d,具有预防AAD发生的作用(NNT=10),早产儿应用上述其他益生菌制剂预防AAD结论是有效和安全的。益生菌耐受性较好,偶有轻微副反应,如皮疹、恶心、腹胀、腹鸣或便秘等。欧洲儿科营养学会(ESPGHAN)益生菌预防AAD工作组的结论与Cochrane一致,其他益生菌菌株或复合菌株制剂缺乏有效的证据[5]。
2013年美国胃肠病联合会指南指出:益生菌能够有效降低AAD,但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益生菌能有效减少CD感染的发生。在临床不能避免使用抗生素的情况下,益生菌可以作为一种预防措施[16]。Cochrane一项Meta分析研究报告纳入23项完整RCT,共4123例受试者,结果显示,益生菌组CDAD的发生率为2%,安慰剂组为5.5%(RR=0.36;95%CI0.26~0.51),益生菌显著减少CDAD发生风险[16]。最新一项Meta分析结果显示,LGG和布拉格酵母菌减少CDAD发生风险,减少率分别为63.7%和58.2%[17]。粪菌移植是艰难梭菌感染(CDI)复发患者的一种治疗选择,通过供者粪菌移植重建患者肠道菌群平衡[1]。
综上所述,抗生素导致肠道菌群紊乱,益生菌干预的最佳时机是致病菌繁殖或定植前,因此,益生菌早期干预可以有效减低AAD和CDAD的发生率,临床上在使用抗生素同时应用益生菌是合理有效的。益生菌用于预防的效果与抗生素的种类、抗生素的疗程、患儿年龄、住院时间以及并发症等危险因素有关,益生菌的数量和菌株对疗效也有一定影响,推荐剂量为≥5×109CFU/d[5,16]。
免疫调节。
健客价: ¥168免疫调节。
健客价: ¥33.79调节便秘呵护肠胃增加免疫力
健客价: ¥258儿童钙铁锌多维益生菌粉,补充钙铁锌及多种维生素等全面营养。有助于儿童生长发育和宝宝的食欲,更有助于皮肤健康。
健客价: ¥258买2送1 买5送3送的都是原品
健客价: ¥128促进肠道消化系统健康,预防生殖系统感染,增强人体免疫力,帮助吸收营养成分,降低血清胆固醇,预防或改善腹泻。适用人群:18岁以上成人、容易出现腹泻等问题的人群、 排便困难的人群 、肠道菌群失调的人群、 高脂饮食的人、平时少食牛奶或乳制品的人群。
健客价: ¥250调节肠胃,促进吸收, 提高免疫力, 防止尿路感染。
健客价: ¥229买2送1 买3送2 送的都是原品 4瓶1个周期 8瓶巩固装,医师建议按照周期购买
健客价: ¥158增强免疫力。
健客价: ¥198适用于通便利尿、清理肠胃、预防“三高”。
健客价: ¥288买套餐更优惠 修正推荐 旗舰店品质 修正的 良心的 放心的 管用的
健客价: ¥258调节肠胃,促进吸收, 提高免疫力, 防止尿路感染。
健客价: ¥139调节肠胃
健客价: ¥1981.成年人及儿童急、慢性腹泻。 2.用于食道、胃、十二指肠疾病引起的相关疼痛症状的辅助治疗,但本品不作解痉剂使用。
健客价: ¥241.成年人及儿童急、慢性腹泻。 2.用于食道、胃、十二指肠疾病引起的相关疼痛症状的辅助治疗,但本品不作解痉剂使用。
健客价: ¥241.成年人及儿童急、慢性腹泻。 2.用于食道、胃、十二指肠疾病引起的相关疼痛症状的辅助治疗,但本品不作解痉剂使用。
健客价: ¥22.5调和肝脾,涩肠止痛。用于肝脾不和,泻痢腹痛,慢性非特异性溃疡性结肠炎见上述症候者。
健客价: ¥12调和肝脾,涩肠止痛。用于肝脾不和,泻痢腹痛,慢性非特异性溃疡性结肠炎见上述症候者。
健客价: ¥26调和肝脾,涩肠止痛。用于肝脾不和,泻痢腹痛,慢性非特异性溃疡性结肠炎见上述症候者。
健客价: ¥16.5治疗消化性溃疡,特别是幽门螺杆菌相关性溃疡,亦可用于慢性结肠炎,溃疡性结肠炎所致腹泻及慢性浅表性和萎缩性胃炎。
健客价: ¥34本品适用于治疗消化性溃疡,特别是幽门螺杆菌相关性溃疡,亦可用于慢性结肠炎、溃疡性结肠炎所致腹泻及慢性浅表性和萎缩性胃炎。
健客价: ¥31